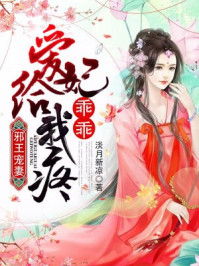橋洞下冒出容貌平常的護衛,認真的看着鳳知微的背影,道:“兩種可能,一是破釜沉舟,回府抗争;一是委屈求全,俯從秋府意志。”
他笑笑,指了指身後十裡煙花,道:“總之,她會立刻回去,絕不會在這煙花地流連太久,多呆一刻,便多污一分聲名,她總不能拿自己終身開玩笑。”
“是嗎?”男子微笑,拖長聲調。
“打賭。”甯澄興緻勃勃湊過來。
男子不置可否,兩人站在橋上,看見那女子一路直行,似乎有目标般毫不猶豫,随即在一處挂着蘭花燈的門前停下,紮起男子的發髻,然後,幹脆的敲門。
甯澄的臉青了。
那女子臉微微側着,對着開門的人微笑說了句什麼,裡面的人似乎愣在那裡,而讀懂唇語的甯澄,遠遠的在橋上,猛地一個踉跄。
橋上,男子突然輕笑。
他墨玉般的瞳,閃着新奇而銳利的光,像是久已沉靜的深淵,被長天之外帶着雪意的風,吹起層波疊浪。
他立在橋頭萬丈紅日裡,黑色披風上淡金曼陀羅花在風中飛揚,那烈烈冷風吹來遙遠的語聲,他似乎聽見風裡,那纖弱的少女,對着開門的蘭香院老鸨,詢問得冷靜而瘋狂。
“你這裡,需要龜奴嗎?”
“小知,聽說集市上新出了挑染絹花,給我帶幾枝!”
“也給我帶幾朵,要翠綠橘黃的!”
“四芳齋冰糖糯藕帶半斤!”
時近中午,十裡胭脂臨近蘇醒,蘭香院小樓莺聲燕語,姑娘們紛紛探出身,招呼着樓下天井裡,挎着籃子準備出去采買的青衣小厮。
小厮是蘭香院紅牌姑娘茵兒的遠親,一個月前投奔來此,不多話,卻靈活有眼色,很得姑娘們喜歡。
“嫣紅姐姐膚色白裡偏紅,戴翠色花兒反而相沖,不如淺粉,更增麗色。”小厮仰頭含笑,又道:“糯藕雖好,吃多了卻積食,翠環姐姐太貪吃,小心成了肥美人。”
“臭小子!”姑娘們笑嗔,神情卻是滿意的,嫣紅笑道:“小知,要不是你是茵兒遠親,又在我們這地方打雜,我真要以為你是哪家大戶人家的公子出身。”
“可能嗎?”茵兒從房内出來,一拍她肩,“我天盛皇朝等階何等森嚴,大戶人家公子就算淪落成乞丐餓死,也不會來我們這地方的。”
她神色複雜的看了那小厮一眼,對方對她微微一笑,依舊坦然,正如這人一直以來的氣質――似乎明朗,其實神秘,似乎冷靜,其實行事超越常規。
小知,人緣極好的魏知,鳳知微。
托庇妓院一月來,她将打雜的工作勝任得很好,當然這也多虧了茵兒的照顧,那女子沒讓她真去做龜奴,纏着媽媽收了她做小厮,雖說其實于事無補,但好歹也是一份善心,鳳知微十分領情,茵兒卻對她謝了又謝,說那日實在是救命之恩。
不過是伸手拉她出河,怎麼就嚴重到救命之恩,鳳知微不解,茵兒卻閉口不答,她對那晚的事心有餘悸,提起那男子便神色驚恐,看那驚恐,并不像是因為被推入河,倒像還有些别的。
鳳知微卻沒有再問下去的欲望,那夜橋上共飲,雪夜一别,她并不願與他再見。
然而世事總會事與願違――不是不想見便可以不見的。
她挎着籃子,剛要出門,突然看見前方來了一大群人。
鳳知微一怔,剛想躲,那邊已經有人招呼道:“喂,那龜奴,公子爺們來了,還不安排姑娘接客!”
鳳知微低着頭,眼角瞥到那些人衣着華貴,顯見都是京城王孫公子,其中一襲錦袍,月白重錦,衣角繡銀線竹紋,清雅高貴,那色彩看得她眉梢一動,頭登時垂得更低。
一邊側身讓開,一邊轉頭,啞聲對院内喚道:“姑娘們,有客……”
這一聲還是平時聽龜奴張德迎客學來的,不熟練,腔調有些僵硬,那群王孫公子頓時轟然大笑。
“蘭香院哪來的新龜奴?連迎客都叫得像娘們叫春。”
“張德哪去了?換這個磨磨蹭蹭的小子?”
一群人旁若無人從她身邊笑着過去,鳳知微盯着地面,見那襲袍角也點塵不驚的掠過自己身邊,剛無聲的舒了口長氣,就聽一個公子哥兒笑着指了她,對迎來的媽媽道:“等下我們要吃酒行令,叫這小子侍候着!”
媽媽愣了愣,勉強應了,使個眼色示意鳳知微過來,低低道:“小心些!唉……”
媽媽神色憂慮,毫無生意上門的喜色,鳳知微詫異的看她,媽媽神色凝重,低聲道:“看見那個黃衣服的瘦子沒?聽說不是個東西,前頭冠華居的頭牌軟玉兒,據說被那家夥弄殘了,冠華居苟媽媽仗着有人撐腰要鬧,沒幾天被人逼得連院子都砸了關門,唉,怎麼今天想到來這裡?可不要給我生事……”
又囑咐鳳知微:“小知,你向來伶俐懂禮,比院子裡其他人都強,今天可得幫媽媽一回,好歹照看着。”
鳳知微無奈應了,寄人籬下,還寄在妓院,這一日是遲早的事,能躲自然要躲,不能躲,那便走着瞧罷。
那一群人占了院裡最好的“倦芳閣”,叫了最美的姑娘來陪,人手一個,嬉笑戲谑,吵嚷得不堪,卻隻有一處角落,人人都自覺的不去打擾,顯得安靜得有些詭異。
他所在的地方。
一方黑檀繡銀竹屏風半隔出甯靜空間,精緻毯席旁,三足黑石小鼎裡燃着上好的沉香,淡白微涼的煙氣裡,那人長發微散,衣襟垂落,以肘懶懶支着腮,笑意淺淺俯首于姑娘皓腕玉指間,飲了她奉上的杯中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