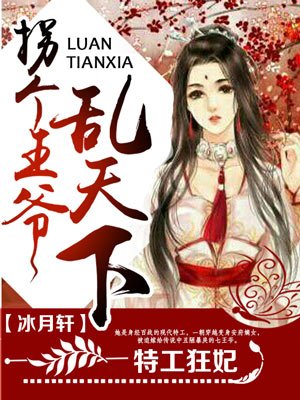第068章你――該死!
天空的小雪粒漸漸變大,最後變成鵝毛大雪。
就連馬兒也凍的打了幾個響涕。
山頂。
幾株蒼茫勁松長在崖邊,皚皚白雪落在其上,倒是讓這幾株松樹無端生出了一種夢境般的感覺。
這場景倒是讓安以繡想到白居易所做的《澗底松》。
铮铮鐵骨傲蒼穹,
霜雪奈何不動容。
滿目山河無障礙,
且登高處一盤恒。
安以繡随意的坐在石頭上,自上而下眺望着遠方的月亮。
沐淵白在白馬頭上拍了兩下,坐在安以繡身邊:“王妃覺得這處風景如何。”
這怕是附近最高的一座山,能一覽衆山小,确實是個好地方。
“每當本王心情煩悶的時候,便會來這邊坐坐,王妃是本王第一個帶來這裡的人。”
沐淵白不知道什麼時候從袖袋裡掏出了一個酒囊,打開蓋子喝了幾口,然後看向安以繡,将酒囊遞給她:“天氣嚴寒,王妃也喝幾口祛祛寒。”
安以繡确實覺得冷了,接過酒囊喝了一大口,倒的急了,一時間嗆得咳起來,好一會兒才回過神。
這酒釀了一定年頭,度數高,喝一口便上頭,她擺了擺手遞給他笑道:“你什麼時候藏了酒?竟不知你還嗜酒。”
沐淵白望着遠方,眼神悠遠:“不,隻為敬英靈。”
國家的安定離不開那些浴皿奮戰的将士,但是時至今日,又有誰還會記得那些逝去的英靈?
安以繡轉頭看着沐淵白的側臉,雖然看不清他的面孔,但是從他身上散發出的情緒,讓她能感覺到他現在的……悲痛。
她撐着下巴,沒有說話。
今天到過那個小院,看到那些無父無母的孩子,安以繡對于沐淵白的讨厭少了幾分。
都說喜歡孩子的男人是善良的。
他如今的悲傷也不似作假。
雖然他那次想至她于死地,但也如他所說,她确實活了下來。
這永遠是她心中的芥蒂,但至少在其他方面,她對他的看法變了幾分。
也許是喝了酒,心中有些壯膽。
安以繡問:“為什麼傳聞說你殘暴弑殺?”
這是她一直較疑惑的問題。
傳聞皆說他暴躁弑殺,她也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隻要他有任何異動,她絕對不會手下留情。
可是自從嫁給他,她沒有見他有過任何暴躁的行為,感覺他總是在笑,雖然她感覺,他的笑并沒有到心底。
更多的是一層僞裝。
比她更甚。
沐淵白又喝了一口酒,然後将酒塞塞回瓶口,拿着酒囊在手中左右抛着。
就在他要說話時,一陣狠厲的風聲帶着殺氣直奔沐淵白後心。
沐淵白眼神一凜,瞬間閃開。
長箭射空,直沖崖下墜去。
安以繡也在一瞬之間站起,轉過身,眼神盯在不遠處那一群黑衣人身上。
領頭的黑衣人身穿鬥篷,面上也戴了張面具,不過是銀灰色,與沐淵白的黑色面具相比,那個銀面具更顯眼幾分。
怎麼她遇到的這些人一個兩個都愛戴面具,為什麼不敢露出自己的廬山真面目,是有多見不得人?
若是有人要易容他們,都不用化妝,直接找個身形和他們相似的人,戴個面具就好。
沐淵白慢條斯理的将酒囊放入袖袋中,沉聲道:“閣下似乎對本王很感興趣?上次抓采薇也是你的人?”
尊少主桀桀笑起來:“是啊,本尊想要你的命很久了。”
這夥人為什麼一直對沐淵白有殺心?
既然這個人他想殺沐淵白,為什麼上一次不動手。
安以繡覺得,如果她是殺手,就不會三番四次的動用組織的力量來做無用功,能一次解決的麻煩絕對不要再來第二次。
沐淵白把安以繡扒到一旁:“那便看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了!”
尊少主見到了沐淵白的動作,忍不住笑起來:“喲,沒看到,這邊還有個嬌滴滴的小美人呢,本尊最喜歡美人了。”
聽到這個銀面男的聲音,安以繡就有些作嘔。
這個人說話的聲音就是讓她很不舒服,他的嗓子似乎被什麼給毀掉了,說話的聲音帶着幾絲沙啞,聽上去就像是破舊的磁帶在地上劃拉的音質。
相比之下安以繡覺得沐淵白正常許多,雖然會出言調戲她,但至少沒做太過出格的事。
尊少主還在繼續說話:“美人,隻要你過來我這邊,我一定不殺你,反而會給你數不盡的榮華富貴,你看如何?”
安以繡皺起眉頭,兇道:“你閉嘴,聽你說話耳朵都要聾了。”
他聲音一頓,語氣變得陰鸷:“敬酒不吃吃罰酒,既然如此,那你就陪他下地獄吧!”
尊少主話音落下,他身後的黑衣人全都舉起了長弓,箭頭紛紛對準他們兩人,似乎隻要尊少主一聲令下,他們就會将手中長劍悉數射出。
尊少主不知道想起了什麼,又舉起手,示意他們等一會兒。
他向前走了幾步,距離沐淵白十來米的樣子停下:“對了,我還要和你說一件事,不然等你下了地獄都不明白這事,豈不是讓我有種無用功的感覺?”
沐淵白冷冷看着他,沒有說話。
“聽說你最喜歡在除夕夜去那一座小院子看看那些小孩,我剛剛也見到了,他們确實天真可愛,臉上洋溢着的笑容讓我都不忍心摧毀他們……”
沐淵白臉色漸變,嘴唇緊緊抿起,似乎已經預示到這個銀面男接下來要說的話。
看到沐淵白的微表情,尊少主顯然很是開懷,一字一句道:“但是本尊怕你一個人在地下孤苦伶仃,便讓他們先一步下去陪你了,你覺得本尊是不是太好了?”
似乎是回想到了剛才的畫面,尊少主哈哈哈的笑起來:“那一張張驚恐的面孔,還有鮮紅色的皿從他們脖子裡和嘴裡流出來,染紅了雪白的土地,那模樣……本尊真想讓你親眼看看……可惜本尊帶不過來,隻能用語音轉述給你聽了……”
沐淵白拳手緊握,手背上青筋暴起,咬牙切齒,仿佛想将這個男人撕成碎片:“你――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