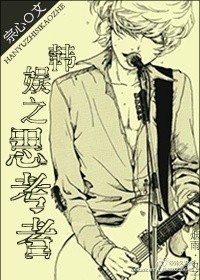帝王受:軍師,攻身為上 第218話兩個故事
宇文焘的話讓宇文盛隆愣了一會兒,好半天才反應過來,隻見那孩子雙手握成拳,直直地看着他,眼裡是一絲不易被察覺的倔強,似乎是在告訴自己,沒有關系。宇文盛隆心底微微一疼,他是決兒的來世,其實也就是他的孩子,這有什麼區别呢?這孩子潛意識裡告訴自己,自己是不被接受的,所以在被拒絕的時候也無所謂傷心,他用倔強來掩蓋自己的脆弱――這讓宇文盛隆心疼。俗話說,會哭的孩子有糖吃。這孩子正是因為強大,所以才讓人忽略了他也需要肩膀依靠。想到這裡,宇文盛隆微微笑了起來,伸手拍了拍宇文焘的肩膀,“雖然你不是決兒,但你仍然是我的孩子,當然,前提是你能接受我這個做了那麼多錯事的父皇。”
宇文焘一震,他看着男人的眼神很複雜,但最終都被一種感動取代,他就那樣看着男人,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
宇文盛隆笑了笑,巧妙地化解了尴尬,“你跟我說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宇文焘沒想到,他竟然也有這樣的耐心,将一切娓娓道來,竟然一點不耐煩都沒有,那些他和阮阮在一起的過往,他從來沒有跟誰細緻地講述過,這是第一次,有人聽他講,那些心酸那些苦痛還有那些幸福,原來有人願意聽而你又願意講,是這樣美好的一件事。
宇文盛隆一直帶着那種淡淡的笑意看着面前的孩子,兩人一個靠在床上,一個坐在床邊,一講就是一整夜,等宇文焘驚覺時,天都亮了,他竟然像個老頭子一樣絮絮叨叨說了一整夜,還是對着一個大病初愈的病人,真是該死!
宇文盛隆聽完這個漫長的故事後,問的第一句話卻是,“你和那個孩子,現在都好嗎?”
宇文焘覺得有點丢臉,他想自己是太久沒有休息了,所以才覺得眼睛有些疼,他站起來,扶住宇文盛隆,“你歇會兒吧,你大病初愈,我卻拉着你說話,是我的不是了。等你好一點,我帶他來見你。放心,我們很好。”
宇文盛隆點點頭,順從地讓眼前的孩子給他蓋上錦被,“我曉得他會待你好的,從我那次進你的寝宮被他發現,我就知道,如果我走了,他會照顧你,而且比我照顧得更好。”
宇文焘想了想還是問出了那個問題,“天命說我和阮阮世代糾纏,想必即使我和阮阮回去了,恢複本尊的宇文倉決還是會和阮子衿在一起,這樣沒關系嗎?”
宇文焘這句話,似乎觸動了宇文盛隆心底什麼悲傷的往事,隻見他突然不再說話,滿目悲涼,不知在想什麼,宇文焘隻是靜靜地站在那裡,等待。良久之後,方聽到那似乎一瞬間就蒼老了很多的男人開口道,“同為男子又何妨,這世上最大的幸福莫過于,當你從漆黑的夜裡醒來,你最愛的人就睡在你枕邊。如果我早些明白這個道理,也不用這麼多年孤枕難眠了。”
宇文焘一聽,就知道這又是一個故事的開始,他看了男人一眼,有些擔心男人的身體,卻被男人看透,男人對他招了招手,“我剛剛聽了你的故事,你是否也願意聽聽我和我愛人的故事?”
宇文焘重新坐回床邊的凳子上,給人掖了掖被角,安靜地聽着。
“那年,她才十六歲,太後壽誕時,獨自一人跟着表演隊伍混進了皇宮,哪知她實在太笨了,空有一身絕世武藝,卻在偌大的深宮裡迷了路。我看她一個人在禦花園裡急得團團轉,心裡覺得好笑的同時,也覺得有趣,遂決定去逗逗她。我換了侍衛的裝束去接近她,她太容易相信人了,跟着我在皇宮裡轉了一個晚上,才反應過來我是在逗她,當下惱羞成怒,舉劍就向我砍來,卻在要傷到我時,又心軟地收了回去,我當時就想,啊,這就是我要的人,這就是要陪我生生世世的人啊。
“我生來富貴,猖狂慣了,壓根兒不知道人心是最不可能被禁锢的東西。當時的我确認了要将她留在身邊的心意,根本不去管她的來曆,就吩咐暗衛将她扣下了,并且不顧她的意願強行與她有了夫妻之實。我以為,女人嘛,隻要有了夫妻之實,她自然就乖順了。事實上,那之後她确實也安靜了許多,讓我一度失望地以為她已經對我死心塌地了,所以過了新鮮期之後,我又開始流連于其他妃嫔處,那時她還隻是個美人,未經傳召根本不可能見到我,待我再想起她來時,發現她竟然已經懷了我的孩子。
“那是我第一個孩子,可想而知,我有多高興。從那之後,我又日日與她在一起,覺得世上再沒有比這更快活的事了。并很快冊封她為婕妤,我想着,等孩子出生,母憑子貴,我也就能順勢冊封她為皇後了。
“愛戀中的人總是把事情想得過于簡單和美好,幸福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很久。我聽信了妃嫔的讒言,以為她一直處心積慮要殺我,畢竟是我斬殺了她的父親。我想着,我如此寵愛于她,卻換來她毫不留情的背叛,憤怒和痛苦蒙蔽了我的雙眼,原本說好要陪着她直到孩子出生的我,日日流連于各色美人處,有時候甚至幼稚地帶着那些美人到她面前耀武揚威,看着她一日日消瘦下去,心裡有一種變态的滿足感,就更想變本加厲,非讓她知道沒有了她我會過得更快活。可是天知道,每天夜裡在陌生的氣息裡醒來的我,是多麼地想她。
“男人是一種可悲的動物,他總把那些驕傲啊自尊什麼的也一股腦搬到情愛裡,但實際上,情愛裡不需要這些東西。可笑的是,那時候的我并不明白,我隻想着,一定要逼她先妥協,隻要她跪着來求我說她錯了,我一定會原諒她,我覺得作為天子,這已經是我最大的讓步了。可是,她沒有。盡管悲憤欲絕,但她仍然沒有主動來找過我。直到生産那天,因為我的混賬,害得她一個人在凄風苦雨中生下了孩子。那天,我鼓起勇氣去看她,我想,我們的孩子出生了,這應該可以成為一個和好的契機。然而剛一見面,她二話沒說舉着劍一舉刺中我的兇口,我以為她生産力竭,才沒有力氣一劍刺死我,頭一次妥協的我卻換來這樣的對待,我當時的心情不言而喻,隻曉得,那些嫔妃說的果然是真的,這個女人時時刻刻都在計劃着如何要朕的命。我氣瘋了,但到底舍不得對她痛下殺手,隻吩咐把人連同孩子打入冷宮。那個時候,我不曉得,冷宮對于一個正常女人來說都不亞于人間地獄,何況是一個剛剛生産完的女人。我拂袖而去,再也沒有去看過她。直到一年後,她去世。我不知道,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年,她是怎麼度過的。當我破舊但卻幹淨的棉被裡抱起她冰冷的身子時,她的臉色很平靜,一點都不猙獰,那一刻,我聽到自己的心死亡的聲音。我想過,跟她一起走的,但是那個蜷縮在棉被裡哇哇大哭的孩子勾回了我的神智,那是我和她的孩子,我可憐的孩子,寒冬臘月裡已經快三天沒有吃東西了,他不曉得那個躺在他身邊的母妃已經不能再給他東西吃了。一個男孩子,哭起來的聲音細得跟貓一樣,我突然有了活下去的欲望。這是她留給我的最珍貴的寶貝,我一定要好好保護他,我想,如果我做到了,百年之後下去見她,她一定會原諒我的。”
故事太長也太悲傷,宇文盛隆的聲音低得不能再低,很多事情,他是直到她走了幾年後才想明白的,那日刺中他兇口的那一劍,根本不是因為什麼力竭,隻因為她不舍得,雖然恨他,但仍然不舍得,因為她也同樣深愛着他,否則不會給一個與她有不共戴天之仇的男子孕育孩子。他想,在生下孩子的那一年裡,她一定每天都在等他。也肯定想過,帶着孩子一走了之,畢竟她功夫那麼好,想逃離皇宮那還真不是一件難事。但她一直在期待,或許他這個狼心狗肺的男人會突然醒悟而回去找她。然而,那個男人卻一直被自己困在怒火裡,總以為一輩子還很長,可以讓他去慢慢去想開。擁有她的日子很短,卻成為了他這生最漫長的記憶,也是因為她,他頹廢了,才使得後宮那些人有了可趁之機。嚴格說起來,他不是一個好皇帝,因為那個時候他想,江山社稷有什麼所謂,他隻要想盡一切辦法,保他的孩子平平安安就好。隻是雙拳難敵四手,他能信任的人太少了,所以才落得被皇後和二皇子下了毒,讓那母子倆和背後的藍楸瑛以為已經将他控制在了手心裡,隻等除去太子就可以入主天下。到最後,他撐着破敗的身子,隻想着要給兒子留一條好的後路。壓根兒沒想到,還能有機會從頭活一次。
宇文盛隆确實有些累了,他擡起頭虛弱地看着面前靜靜聽着的孩子,這孩子眼角眉梢都像她,很多個夜裡,他看着這個孩子時,就會覺得是不是她回來了。他最後說,“能在一起時就好好在一起,不要去管什麼世俗道德,愛是愛情是情罷了,與旁人無關。”
宇文焘點點頭,“你累了,明天再睡吧。”
宇文盛隆笑了笑,“我總算可以睡個好覺了,這些話壓在我心裡十多年了,一直找不到人說,今天終于說出來了,心裡頓時覺得好受了很多,謝謝你,孩子。”
被男人一口一個孩子,宇文焘卻并不覺得别扭,隻因為男人這樣叫他的時候,真的是一個父親的口氣。确定床上的人已經呼吸平穩,宇文焘才關上門,走到了院子裡,侍衛們安靜地站着,周圍很安靜。宇文焘卻開口道,“閣下來了這麼久,是否還不準備現身?”
侍衛們一驚,這才曉得有人潛進來了,他們竟然絲毫不知,當下個個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
隻見一個藏青色的高大身影從暗處現了出來,那人一臉的絡腮胡子,看起來格外豪放大氣,他笑着打量着宇文焘,“原本以為你功夫平平,沒想到人倒是機靈。”
宇文焘揮手道,“你們都下去。”
那人挑了挑眉,“讓他們都下去,你不怕你我是來殺你老子的?”
“如果你要殺我父皇,易如反掌,他們在不過是多幾具屍體,何況如果你真的是來刺殺皇上的,似乎也用不着一藏藏一夜,隻為了聽個故事?”
“小子,你來世的腦子比這世聰明嘛!”男人笑着走近,毫不客氣地一巴掌拍上宇文焘的肩膀。
宇文焘沒有躲,隻是皺了皺眉,這男人力氣也太大了。“不是來世的我聰明,隻是因為經曆不一樣罷了。想必,你就是我父皇那位從來沒有露過面的至交好友了?”
“跟聰明人說話就是好,能省不少口水。”男人晃了晃腦袋,“這該死的胡子,應該好好刮一刮了。”
“他身體已經沒有大礙,剛剛睡着了。太醫說調養個半年,也就能恢複成常人模樣了。”
男人呵呵笑了笑,“左右他是你老子又不是我老子,不用跟我說得這麼詳細,隻要知道他死不了就好。”
“你不去看看他?”宇文焘見男人轉身就走,不覺開口問。
“我想,他應該并不想見到我。”男人原本豪邁的聲音猛然低沉下去。
“一個人能在絕望中支撐那麼多年,我想除了放不下他的兒子以外,應該還有别的牽挂,隻是或許他自己還并不明白。”宇文焘看着男人高大的背影,已經管了這檔子閑事,他也就索性管到底了,“即是有機會又為什麼放棄?上蒼不是每次都這麼好心,會給人重頭再來的機會。”說完,也不管男人突然僵立的背影,宇文焘轉身離去,并吩咐侍衛在宮門外把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