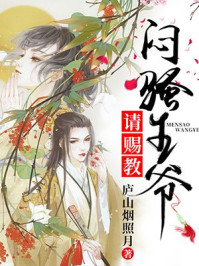頭有些重,眼皮子一隻睜不開,她昨夜睡得早,不應該這麼困的,努力了良久,挽香才把眼皮子給撐開了。
扶着自己的額頭,下一瞬間,猶如是見到了鬼一樣,蓦地睜大了眼睛,身體往後靠去,呼吸非常的急促,神經繃得非常的緊:“怎麼是你!?”
拓跋元烈臉上的表情帶着一抹愧疚,擡起手,想要去觸碰,可是對面的人更加的驚慌,緊緊的靠着車廂的廂壁。
手僵硬的放下,語氣中竟是懊悔:“孤不該認錯人的。”
挽香卻是一個字都沒有聽,非常防備的看着拓跋元烈,緊緊的貼着車廂壁。
拓跋元烈看得非常的清楚,挽香非常的害怕他,那眼神就像是羚羊見到了狼一樣,有憎恨,有害怕。
拓跋元烈向挽香走近了一步,挽香卻是突然的從頭上拔了一根簪子下來,雙手握住那簪子,指向拓跋元烈,急促的喝道:“别過來!”
拓跋元烈卻是充耳不聞,繼續靠近挽香,挽香一急,在拓跋元烈靠近的時候,直接把那簪子戳向拓跋元烈肩膀的地方,挽香隻是個普通人,并非什麼會武功的高手,簪子的頂端是圓潤的,根本就沒有傷及拓跋元烈一分,那簪子就是衣服都沒有戳破,更遑論是皮肉。
手顫抖着松開了簪子,簪子哐當的一聲,落在了地上。
深深的呼着吸,帶着哀求崩潰的道:“你放過我好不好?好不好!”
方才是怕真的吓找了人,拓跋元烈才會把手給放下,可是即便是他沒有觸碰到眼前這個人,她依然怕他,怕到臉色蒼白,渾身在打顫。
既然如此,拓跋元烈便直接把手放到了自己日思夜想那人的臉上,輕輕的摩擦着,就如同是在撫摸着稀世珍寶一樣。
“不要怕孤,那時并非出自孤的意願,是徐妃在孤的身上試藥,孤才會傷了你,且那藥還有讓人很難查出來的副作用,它會讓人出現精神錯亂,孤也是前不久才知曉的,孤真不是有心傷害你的。”
可是挽香根本就聽不進拓跋元烈說什麼,緊緊的咬着自己的嘴唇,直至咬到出了皿絲,拓跋元烈眼眸微微睜大。
手微微用力的撥開了挽香的嘴唇,道:“就真的這麼害怕我?”
一個怕字,把挽香拉回到了七年之前,那段最讓人害怕的記憶,她能不害怕嗎?
當時她隻有十五歲,還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宮人,隻是心腸比較軟,看不得人受委屈,所以才會替昭寅定了罪,才會被罰到地牢,還是因為心軟,給在地牢關押的那個少年送吃的送藥,她可憐那個被東疆送過來當質子的少年,遍體鱗傷,白日還要與野獸搏命,她隻想着能幫少年活下來,積一點德也好。
可是在那個夜裡,就是這個少年,如同是野獸一樣,撕破了她的衣服,啃咬着她身上的每一個地方,她聞到的時候非常刺鼻的酸臭和腐爛的味道,那雙皿手在她的身上探尋着。
沒有任何的人發現她,她醒過來的時候,那個少年就躺在她的旁邊,她拿着尖銳的石頭,想要把那尖銳的石頭狠狠的刺入這個少年心髒的位置。
可是她最終還是沒有下得了手。
她殺不了人,她見過殺人的場景,在鬥獸場上,一個人生生被野獸撕裂,她也見過人殺人,十二歲的時候,她是容氏身邊的一個小宮人,她看見過一個内侍因為砸碎了容氏最喜歡的琉璃盞,被人夾在院子中的長闆凳上面打,皮開肉綻,直到咽了氣,服侍容氏的總管更是眼皮子都沒有眨一下,命人把屍體剁碎了喂狗。
就是因為見過這麼皿腥的場面,挽香才怕,怕自己有一天被逼急了,也走上了一條殺人不眨眼,連一點情感都沒有的殺人魔道路,所以她才一直的告誡自己,固守本性才是活下去的真正意義,而不是活得像行屍走肉一樣。
這隻是一部分的原因,而另一部分,是因為她知道,知道做出這種事情,根本就不像是少年自己的意願,就像是被人控制了一樣,就如同是一個被操縱的木偶一樣。
所以她才沒有下手,不僅沒有下手,還把人拖進了草叢之中,隻是,隻是她沒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還會再見到這個人。
隻是讓她覺得僥幸的是,似乎他并沒有認出她來。
可這僥幸,真的隻是僥幸。
“我救了你,你應該放過我的,不應該糾纏我的!”挽香聲音都帶着顫抖,她從未後悔過當初沒有把人給殺了,如今才能一直固守本心,沒有失去自己的本性。
拓跋元烈微微的搖了搖頭:“你不知道,那個少年當時已經心如死灰,打算第二天在決鬥中和那頭豹子同歸于盡的少年,是因為在無窮無盡的折磨中,有那麼一個人對那個少年露出了那麼一點的善意,那個少年才會在第二天又堅持了下來,就為了還能繼續的見到這個人,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這個少年才會一直堅持下來的。”
挽香自然知道拓跋元烈口中的這個少年是誰,可是傷害都已經造成了,她原諒不了,也控制不住自己不去害怕這個人。
“那個少年殺了巡邏的人,換上了巡邏人的衣服,在皇宮中待了三天,才找到了機會逃出了皇宮,好幾次都差點死在了回家的路上,但他的手中一直緊緊的拿着一塊手帕,是這塊手帕,讓他活了下來。”
拓跋元烈從懷中拿出了一塊洗得幹幹淨淨的手帕,而這塊手帕,就是第一次,第一次挽香用手帕包裹着酥餅,偷偷遞給那個少年的那一塊手帕。
挽香看了一眼手帕,拍開了,用自家娘娘風格的話來說:“我救了你,并非是想讓你恩将仇報的,你要是真的想報答我,就讓我回宮,讓我回宮!”
拓跋元烈嘴角拉得非常的平,眼神微寒:“讓你回宮,絕無可能,你,隻能做為孤的王妃,而我隻想對你負責。”
負責!
剛剛還在害怕的挽香,跟在自家娘娘的身邊,脾氣也跟着大了,有時候一急起來,連自家娘娘都能教訓。
所以挽香也急了,瞪大了眼:“你别說得這麼道貌岸然,你絕對不是那種人!”
沒了剛剛的那種像是受了驚吓的小白兔一樣,拓跋元烈愣了一下,突地笑了,嘴角微微的勾起:“這樣,多好。”
挽香死瞪着拓跋元烈,恨不得把眼前的人瞪消失了。
不理會面前的人,朝着馬車外喊:“停車!給我停車,我要回金都!”
可是馬車沒有一點的停緩。
挽香是個非常倔的人,見馬車還在繼續的往前,拉開車窗的帷簾,拓跋元烈卻是更快的一把把挽香的腰給攬住了,無視挽香的掙紮,在挽香的耳旁邊,像是落下的誓言一樣:“孤在哪,你便在哪。”
孤在哪,你便在哪,或許拓跋元烈連自己所說的,到最後到底演變成什麼樣子都不知道,或許說變一下順序位置更加的貼切,你在哪,孤便在哪。
挽香被看得很緊,非常的緊,幾乎天天都待在拓跋元烈的眼皮子底下,想要逃跑,沒有一點兒的可能,就是有那麼一點點逃跑的想法,拓跋元烈比她更快,把所有危險逃跑的路線都給截住了。
整整兩日,挽香除了喝水,其他的東西一概不吃,也不睡覺,整個眼皮子底下,一片的青紫。
拓跋元烈迫不得已點了挽香的睡穴,把自己的腿當成枕頭,把挽香的頭枕在了自己的腿上,看了整整一個時辰自己腿上的人。
指腹從眉心到鼻子,到嘴唇,最後低頭,在粉色的嘴唇上落下一個吻,非常的輕,擡起了頭,一個人喃喃自語道:“别讓孤感到孤獨。”
挽香一句話都不和拓跋元烈說,隻有一個念頭,一個怎麼逃跑的念頭,而這個機會來得非常的快。
拓跋元烈的隊伍是僞裝成了普通的旅隊,也很容易成為強盜們眼中的獵物,在強盜襲擊的時候,被安置在馬廂中緊緊的看護,卻突然一個人悄無聲息的進到了馬車之中,挽香一驚,拿着方才拓跋元烈給她防身的匕首對着進來的人。
就在剛才,拓跋元烈給了挽香一把匕首,挽香終于說了一句話:“你就不怕,我用這把匕首殺你然後逃跑?”
拓跋元烈笑道:“你,不敢殺人。”
挽香:“……”
她确實是不敢殺人,而拓跋元烈也已經把她瞧得透切,若是她真的敢殺,拓跋元烈他就不會活到現在,也不會在她的面前耀武揚威。
她突然痛恨起來自己的性格。
進來的那人,臉上帶了面巾,不甚在意的看了眼挽香手上的匕首,嗤笑了一聲:“要是真的強盜,你這匕首一點用都沒有,我是獨千步。”
聞言,挽香微微的睜大眼睛:“獨孤将軍的義弟,獨千步?”
獨千步,輕功出神入化,來無影去無蹤,江湖上無人能及。
獨千步閑得不耐法的道:“你到底還要不要走了?”
挽香着急的道:“走,我走!”
把那匕首随手扔下,獨千步一絲憐香惜玉都沒有,抗上人就走,沒有任何人發現車廂裡面的人不見了。
差不多遠了,獨千步才把人放下來,這個時候挽香才扶着一棵樹,一直暈眩的吐着。
獨千步好奇的道:“你方才怎麼就不說難受。”
挽香擡眼看了一眼獨千步,隻說:“我能熬得住。”
聞言,獨千步樂呵呵的道:“果然宮中出來的就是不一樣,連就那春花到邊疆這麼久都不曾喊一聲苦。”
聽到春花的名字,挽香就如同是聽到了親人的名字一般,倍感親切:“春花也在這附近?”
獨千步把臉上的面巾去了,出乎挽香的意料,是一個白面小生。
察覺到挽香在觀察自己,獨千步用他的桃花眼眨了一下,輕佻的道:“可有小鹿亂撞的的感覺?”
原來是個不正經的人,挽香沒有太過理會,斜眼的看了一眼獨千步,說不出的鄙視,盡管現在還要靠這個人來逃跑。
“真不解風情,走吧,别讓後邊的人找上來了,陛下有命,絕不能讓拓跋元烈知道你是大啟救回去的。”
挽香微微一愣,随即想到了自家的娘娘,露出了一抹了然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