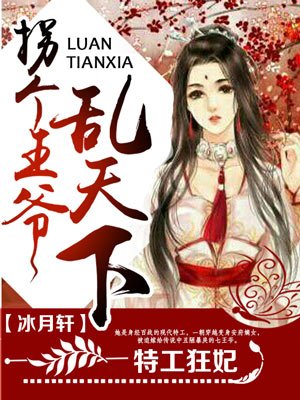崔維桢身處風暴中心,泰然自若,風尚書的視線他盡心洞察,雖然不知他哪來的底氣,但他還是有必要站出來表明立場:“下官盡忠皇差,不失職已是僥幸,不敢企圖風尚書口中的大建樹。隻是未料風尚書對下官寄予厚望,指望我建功立業,您的一片苦心實在讓下官銘感五内,深感惶恐。在此敢問風尚書,如何才能建功立業?請您指點迷津,好教下官日後有前進的方向。”
風尚書被問住了。
若論建立功業,崔維桢絲毫不輸于人,所做的甚至是許多大臣一輩子都達不到的成效,哪裡還需要他的指點?
看來崔維桢不僅僅是背靠一個會做生意的妻子,連嘴皮子也利索得很,這番連削帶打,把他的面子都踩下去了。
風尚書臉上冷色更重:“崔侍郎莫要斷章取義,本官未嘗說你毫無建樹,隻是覺得你最近有所懈怠,好心出言警戒罷了。若是你不愛聽,下次本官不再多言就是了。”
“風尚書言重了,您乃皇上的肱股之臣,下官初出茅廬,許多地方還需向您學習,矜矜業業,以報皇恩。”
崔維桢從袖子裡取出一本厚厚的奏折,輕笑道:“其實風尚書誤會本官了,本官最近未曾躲懶,一直與屬官統計大周戶籍、土地和賦稅的情況,此乃成果,正待上交皇上批閱。”
風尚書也笑了,但笑容卻是說不出的鄙夷和嘲諷:“崔侍郎莫不是糊塗了?你此前不是已經統計了戶籍和土地?為何還要将之與賦稅一起上交給皇上?”
“皇上日理萬機,下官自然不敢叨擾皇上,隻是下官與屬官用了新的法子統計各項情況,特寫成奏折,呈給皇上過目。”
風尚書心覺有異,皺起了眉頭,沒再說話。
戶部尚書李元義正在旁邊,風尚書向其投去詢問的眼神,結果對方臉色微異,看樣子似乎不知情。
李元義任人唯親,任戶部尚書多年,唯獨器重與他同宗的李侍郎,對于崔維桢這個異軍突起的後輩,平日裡也是愛答不理,還時不時給點小鞋穿,彼此關系肯定是不好的。
崔維桢如今做出成果,避開李元義直接呈奏給皇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隻不過,李元義地面上不好看就是了。
即便如此,李元義也不想在朝臣面前丢了作為戶部尚書的面子,面對同僚的疑問,他一律打着太極回答:“崔侍郎的奏折确實所有不同,我一時無法說清原委,大家若是好奇,盡管讓崔侍郎解釋便是。”
李元義給了台階下,崔維桢自然給面子,與衆人說道:“此乃本官受内子啟發的一種記賬方法,以圖表的形式統計各種款項和信息,化繁為簡,一目了然,目前來看,這種法子對戶部最有效用,李尚書看了也都誇好的。”
李元義的面子被t擡了回來,心裡那點兒不舒服勁兒稍稍減了些,他知道崔侍郎不是無的放矢之人,既然都拟折呈獻禦覽了,肯定是個好東西。
為了在同僚面前表現自己不同于風尚書的慈和開明和容人雅量,他一臉滿意地說道:“崔侍郎所言不假,本官已經決定日後在戶部使用這種新式記賬方法了,各位同僚如果需要借鑒,盡管找崔侍郎請教。”
人最不缺的是好奇心,即便是百姓眼中高高在上的達官貴人也一樣,其他部的尚書們都好奇地湊過去詢問,空留風尚書不尴不尬地站在那裡,臉色都漆黑了。
崔維桢身邊很快就湊滿了人,恪王一黨的朝臣不動如風,恪王最近的處境也十分尴尬,主動走到老丈人身邊,與他聊了起來。
風尚書如蒙大赦,雖然他很不滿恪王怠慢他的女兒,但對方畢竟是王爺,還是他政治投資的對象,聊天時還是滿臉笑容的。
宣武帝來到金銮殿時,看到的正是這番熱鬧的場面:“今日諸位愛卿興緻不錯啊,都在讨論些什麼呢?”
皇帝駕到,沒人膽敢藐視聖駕,衆人立馬停止了讨論,迅速回到班次中去。
金銮殿中盡是皇帝的耳目,他來之前肯定已經知道殿中發生的事情,但是皇帝金口一開,肯定是要回答的。
往常這種時候都是魏王接話,這次竟是恪王搶了話頭,道:“啟禀父皇,景甯伯受其夫人啟發,新研究一份記賬圖表,方才正在與諸位朝臣交流呢。”
恪王一臉坦蕩,在場站班的朝臣卻是臉色詭異。
恪王居然主動替崔侍郎邀功?該不會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吧?難道雙方已經冰釋前嫌了?魏王一黨心裡懷疑了起來。
但是,某些朝臣倒是沒有往黨争這方面想,鑒于恪王與甯國夫人的風月一二事,他們不由得想歪了——
恪王給崔侍郎邀功是假,替甯國夫人揚名才是真!不然崔侍郎話裡話外帶上自家夫人也就罷了,他一個外人,何必說得那麼清楚呢?
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不管朝臣怎麼想,很顯然,宣武帝非常吃這一套,他滿意地颔首一笑,道:“甯國夫人素有奇思,崔愛卿才華橫溢,如此相輔相成,正是天作之合。”
宣武帝非常自負,對自己的兒子也相當得偏寵,覺得恪王膽敢在朝臣面前大方地提起甯國夫人,肯定是已經放下執念,改過自新了。
從一個父親的角度來說,他的心裡是非常欣慰的。
他給恪王遞了個贊許的眼神,恪王回以孺幕一笑,這對天家父子的濃濃之情,不知閃瞎了多少雙眼睛。
魏王臉上的笑容淡了淡,果然不能小看了老七,他們母子能夠得寵多年,靠的就是對帝心的揣摩和把握,在這一點上,是其他皇子都比不上的。
不過,再次的寵又能怎樣呢?
所有的情分都是一筆筆消磨掉的,就是不知老七在父皇心裡的情分有多厚,經不經得起他的一遍遍消磨。
魏王轉了轉拇指上的扳指,臉上重新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