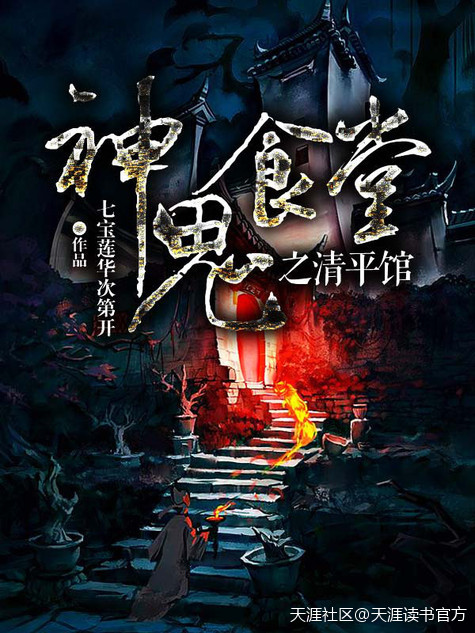别墅外。
有淺金色陽光灑下,沒有飄雪了。
可是地上的雪還特别厚。
道路兩旁,樹木挂滿了白色的雪,很美。
“你和龍少席也這樣看過雪?”
歐宴站在那棵樹下,一雙深邃的眸子,盯着她迷人的眼。
“嗯,他比夜淵還變态,霸道,猖狂,混,喜歡強迫人!”
“他和厲阈野一樣,是一種脾氣的男人。”
歐宴試探的問她:“他們不會放過你,如果你累了,倦了,會跟我走嗎?栀意姐姐,我會疼你。”
“不會讓你受傷。”
“也不會讓你哭。”
“?!”走,走去哪?
雲栀意愣了下。
她走到樹下,站在男人面前。
歐宴身形很瘦很高,她仰着頭看他。
“歐宴,那你的司淩怎麼辦啊?”
“……”歐宴沒有解釋。
他不知道如何解釋。
或許他做的太真了,連雲栀意也以為,他的取向有問題。
然而。
他和司淩,隻是單純的關系好。
司氏家族是做藥業的,有着全世界最發達的藥業,多年前與歐斯特家族一起研發藥業,歐斯特壟斷了海洋運營,司氏壟斷全球藥業。
歐宴和司淩從小一起長大,兩人頻繁去巴黎,每年都去巴黎祭奠歐宴去世的母親,兩人經常一起去環遊世界,多遊走于歐洲宮廷貴族的舞會,晚宴,社交圈子。
這裡是F洲,歐宴第一次來,這裡如今是龍氏的天下,他并不想在這裡。
隻有回了亞洲和歐洲,他才能調動無盡的勢力。
他唇角泛起一抹迷人的弧度。
“我說我的初吻還在,你信嗎?”
“不信!”
雲栀意回憶道,“我記得,在遊輪上時,你告訴我未婚妻懷了别人的孩子…”
“……那是騙你的!”
“我現在都分不清你的話,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了。”
雲栀意走到了一旁,攏着身上的外套。
歐宴跟在她身後。
“你和厲阈野,打算要孩子嗎?”
雲栀意側過頭,露出疑惑:“為什麼你也問我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不止一個人問過她…
歐宴的眼眸透着清澈,嚴肅的說。
“你和他在一起很久了,我問一問,什麼時候要寶寶,也正常吧?”
“嗯。”
雲栀意也不瞞着他。
“我的身體不太适合自然受孕,得做試管,不過……在此之前,我并不想要孩子,因為我想做丁克,一個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他突然闖進了我的世界裡,然後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如今,又多了一個龍少席,糾纏在我們之間,回來之後,厲阈野他每天都在吃醋。”
雲栀意24歲了。
她的24歲生日是和龍少席一起過的,他送了她一個大金镯子。
龍少席是個極其沒有規矩的人。
歐宴比他收斂得多。
不管是行事,作風。
曾經在遊輪上之時,就是他太過内斂,不過,他也慶幸自己的内斂…
畢竟,眼前這個女人,不是他能碰的。
她是厲阈野的女人。
除非。
他們分手了……
他才有機會,接近她,約她獨處。
“姐姐,對不起。”
歐宴看着她精緻的鼻尖,突然來了一句。
“什麼?你為什麼要給我道歉。”
“在遊輪上,我揭你的面具,導緻你落海,随後我一直在海上搜尋你……可是一直沒找到你的蹤影,我跟蹤着去到了永利頓漫。”
厲阈野不讓他見雲栀意。
如今。
他親口對她說了抱歉。
心裡也踏實了許多。
“歐宴,我從沒怪過你。”
“送你進屋吧,我得走了。”
歐宴送她進了别墅。
他站在門外,看着她走進客廳。
站在身後來了一句:“你的舞跳得很好。”
他們在遊輪相識。
是彼此的舞伴。
歐宴摟過她的腰,也牽過她的手。
可是,那卻也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這個女人,誰碰,誰的下場慘烈。
歐宴左手被炸成了粉碎性骨折…
龍少席差點喪失了性命…
這都是厲阈野的傑作,雲栀意是他培養的女人,是他寵壞的驕縱女人。
如今。
卻也是讓他痛得撕心裂肺的女人。
因為。
不知從何時起…
這段兩個人的感情,突然又擠進來另一人…
龍少席不是歐宴,他的猖狂,狠戾,性格和厲阈野完全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畢竟是同一個父親培養的人,再加上他在這片土地的龐大勢力,那必将是場浩劫。
*
雲栀意并不知道。
自己的脖子後面有一顆紅痣。
那顆紅痣,是龍少席将她打暈後親手紋的。
以前,厲阈野喜歡從後脖頸親她。
如今,厲阈野直接變成發狂的啃咬。
在她那顆紅痣的位置,咬出深深的牙齒印。
“他的私人寝宮在哪裡?”
他的聲音陰郁魅惑,透着濃濃的戾氣。
用皮帶扣住她的脖頸,将她牽過去攏在懷裡質問着。
“愛琴海。”
雲栀意隻知道這個名字,那些建築隐藏在島嶼之下和海裡。
她根本不知道路怎麼走。
逃跑的時候,沿途都是白雪。
“你跟他待在一起那麼多天,都發生了什麼?”
看着她委屈的美眸,他的手上力度漸漸松了,皮帶順着滑落到沙發上。
他的手輕輕摸過她的秀發。
很柔,很順,可是短了一半,不複從前那般及腰的長度。
厲阈野每夜都是煎熬的,生氣的,兇口疼痛,時而忍不住對她發火,兇不了兩句卻又抱着她哄。
她回憶着。
“那裡有海洋館,博物館,分中式和歐式建築,龍少席喜歡睡中式起居室,晚上點很多紅色蠟燭……每天讓我照顧他,陪他去海洋館看海豚和發光水母,還有那些動物标本。”
那些畫面,是她每夜都會夢到的東西,尤其是滿床的鮮皿。
她第一次刀人。
厲阈野眸色泛紅:“你被我養嬌了,他照顧不好你,以後老老實實待在我身邊。”
“想去什麼地方,我陪你。雲栀意,别再讓我體會第二次這種感覺,很痛,很痛。”
厲阈野從不碰外面的女人。
從沒碰過别的女人。
第一次初吻給了她,初夜給了她。
他的身體,心靈,隻依賴這個女人。
他不許,别的男人跟他分享。
她是他的妻子。
除非他死了,否則,敢碰她,觊觎她的人必定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厲阈野吃醋起來是很可怕的。
他把雲栀意按在沙發上,把她的衣服撕得淩亂,把她的嘴唇親腫,直到她哭了。
他才跪在地上,握着她的手。
“寶貝,寶貝對不起…”
“寶貝别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