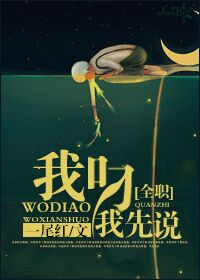中秋詩會開到這裡,也沒多少人有心情再開下去了,面對着甯王安排的精彩歌舞,大家都有些心不在焉了。
趙桓也覺得有些意興闌珊,好好的一個中秋詩會,被一篇坑爹的文章給攪合了。舉起酒杯,簡單的勉勵了這些剛剛考上的舉人們幾句,就率先動身走了。
太子都走了,大家還玩個屁啊,于是一場盛大的中秋詩會不得不虎頭蛇尾地收場了。望着亂七八糟,一地狼藉的院子,趙機欲哭無淚。他想不明白,為啥連續兩次宴會了,都會弄成這種草草收尾的局面?
雖然這場詩會并不完美,但這場卻以極為迅猛地速度傳了出去,兩首兩首風格迥異的新詞和一篇為民請命不畏權貴的策論如風一般擴散。當晚,各大青樓花船就傳出了“醉裡挑燈看劍”和“暗淡輕黃體性柔”的絲竹之聲,而且但凡點曲子的,無不是兩首同點,相互映襯,蔚然成趣。
今夜無眠,無數人都在談論着一個名字,何遠!
忘憂樓後院。
聽着前院傳來的“夢裡挑燈看劍”,素琴秀眉微蹙。今天晚上有些太不正常,自己僅僅是散發出了一點點魅惑氣息,好像就被那個小書生發覺了,如果這可以用先天神識敏銳來解釋的話,那麼能自動擺脫是什麼情況?
若說也是一個隐藏在人群之中的修士,那個小書生又腳步虛浮,氣息散漫,分明沒有任何修煉的痕迹。難不成是自己這段時間太累了,有點疑神疑鬼?
讓素琴百思不得其解的小書生,此時正捧着一本《論語正義》看得津津有味,連睡覺都忘記了。
“怪不得這小子精靈鬼怪,機智百出的,學習起來是真努力啊。”
黃四摸着下巴,一臉的感慨,這小子雖然天天賤兮兮地,但看起書來是真賣命啊,那認真勁兒,一口氣沒有幾個時辰根本停不下來。
“這有什麼好稀奇的,難不成你真的以為他是一個生而知之的聖人?”
張三鄙夷地瞥了黃四一樣,抱着劍,往床鋪上一躺,少操那些有的沒的,難得能混張床睡,我先睡會兒。這哥倆這段時間跟着何遠算是遭大罪了,連個安穩覺都睡不上啊。今天晚上總算可以睡會了――趙桓這裡空房子太多了,而且裡面被褥齊全,這哥倆直接在何遠斜對過找了間客房睡了。不對,是張三睡了,黃四在吃東西,這哥們從廚房順出來一塊牛肉兩碟小菜,吃的一臉的滿足……
“怪不得姐夫才學冠絕金陵,真是勤奮,向來金榜題名的時日不遠了,說不定姐姐很快就要做狀元夫人了!”
陳靜一臉戲谑地打趣着自己的姐姐,惹來陳娴一陣的笑鬧,不過那眼神間卻是透着一股子的自豪。
“什麼狀元不狀元的我真的并不在乎,就算是他隻做一輩子的小書生我也認了。不過說起來也奇怪,你那個夫君到底是什麼來頭,怎麼這麼大的能量?”
陳娴不願意讓妹妹為自己擔心,話頭一轉就轉到了妹妹身上。這趙東實在是太奇怪了,當初看着像一個貧寒子弟,誰知轉眼間人家就買下了這麼大一處院子,那吃穿用度,比自己在娘家時候都要講究。更讓她震驚的是,就是自家那處院子,據說都是這趙東送的,這手筆,簡直無法想象!
“我也不知道,他讓我暫時别問,以後自然會知道。”
陳靜聽到自家姐姐的問話,不由神色有些黯然,哪裡有當人妻子,連人家家庭地址,姓氏名誰都不知道的,她有一點沒說,她現在都在懷疑,是不是連趙東這個名字都是假的。這一天住的,心裡真是不着地啊。
這一夜,并不平靜,無數人都在談論着何遠這個名字。王祯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快月上中天了,夫人楊氏正抱着暖爐坐在客廳裡等他,見他進來,急忙起來結果他身上的披風,一臉關切地問道。
“今日裡怎麼回來這麼晚,往年不是下午就放榜回家的嗎?”
“出了點小情況,有個考生的卷子有點犯忌諱,同僚們起了點争議。”
王祯皺着眉頭坐下來,手指輕叩着桌面,看着有些心思不屬。一看這表情,楊氏就知道自家丈夫肯定是遇到了什麼事了。
“莫非還有什麼不妥?”
“沒有,隻是今日我見到了一個人,十分面善。”
王祯的手指停下來,不過眉頭皺的更近了。楊氏不由放下心來,笑着打趣道:“這千人千面,偶爾遇到一個看上去面善的還不是很正常,有什麼大不了,我呀,看你是這段時間累壞了,才會一驚一乍的。”
楊氏說着輕輕地偎依到王祯的身後,給他輕輕的揉捏着太陽穴。自家這個丈夫啥都好,就是太過較真,有事就喜歡鑽牛角尖。
“不對,我這是第二次見他。第一次在考舍裡見到他的時候,就感覺有些面善,隻是當時考舍内的燈光有些暗淡,我的精力都在他那份卷子上,沒太往心裡去,但我今天又見到了他,他就坐在太子殿下的身邊,我就忍不住多看了兩眼。”
王祯說着說着,語氣忽然變得有些激動,就連那雙手都有些抖動。熟悉自家丈夫的楊氏頓時明白過來,恐怕自家丈夫看到的這個年輕人不同尋常。不由輕柔地把手覆蓋到王祯的大手上,輕輕地拍了拍。
王祯有些感激地沖她笑了笑,示意自己沒事,才強壓着心中的激蕩,緩緩地說道:“那位年輕人竟然長得像極了當年的大姐,而且他也姓何!”
當年王家這段往事在汴京鬧得非常出名,楊氏當年雖然還沒有嫁入王家,但在娘家的時候也聽人說過,還被人戲谑地告誡,“做人莫學王潤娘”。但這事,她卻是沒有辦法插嘴,隻得和聲安慰自家丈夫。
“反正這年輕人還在金陵,他又飛不了,如果你真的懷疑是大姐家的孩子的話,不如我們明日裡就派人前去打探。對了,你可知道那孩子是哪裡人?”
“清遠人士。”
聽到自家夫人的話,他的眉毛才稍稍舒展了幾分。
“清遠?喲,那不是跟寫《将進酒》的何遠是老鄉嘛!要不,回頭我們找他打聽打聽?”
“就是何遠!”
“就是何遠?何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