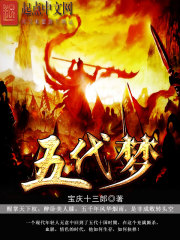讓堂堂才之秀者杜正倫跑來問張德要經濟數據和農業數據,這其實是很滑稽的事情,然而實際上像杜正倫這等精英對具體實務的數據也沒有方向,才是唐朝貞觀年的正常情況。
便是戶口統計,自李唐建立,開元至今已有二十年,其數據彙總還是一團糟。王孝通之流,根本沒有建議權,更遑論決策權。
用一句話來概括,像王孝通老爺子這樣的數據專家,他在貞觀朝的應用數學論述,連專家意見都不算,更談不上什麼專家報告。
唐朝朝廷的組織力,是不如“忠義社”及“華潤号”的。究其原因,這個朝廷還要承擔社會義務,而“忠義社”追求的是利潤,有利潤,就有動力。
如長孫沖之流,倘使張德跟他講大義講德行,大約結果隻會像程處弼狂扁溫挺一樣;而如果張德跟他講茶磚出關在草原獲利翻五倍,大表哥能把借貸記賬法學個通透,還能順便學契丹、靺鞨、室韋、高句麗、新羅、百濟、突厥……十幾種語言。
歡州原本是南交州,即便是一地主官或者軍事長官,對當地風土人情的考察,還是會和漢朝一樣。具體到哪樣東西能獲取暴利,哪樣經過二次加工能獲取暴利,他們是沒有這個主觀能動性的。
一是此事涉及“謀反”,二是他們的主要收益,來源于仕途上的名聲和權力。
聲望可以獲得更多的士族青睐,那麼就能在吸納大量土地及私蓄奴隸的同時,卻又得到同為士族的照拂遮掩。再進一步,聲望可以讓家族的子弟輕易地獲得朝廷的人事任命,因為在和别人同台競争時,考察者首先熟悉的,是你那“賢才”的名聲。
至于是不是吹捧,是不是水貨,那都是任命之後的事情。
那些屌絲逆襲迎娶白富美的戲碼,至少在此時,很難行得通。
馬周途徑洛陽之前,連“洛下音”都沒掌握。宰輔之才尚且如此,遑論那些百裡挑一的人物,隻能淪落為郊縣的刀筆吏,乃至做一輩子貨真價實的“躬耕南陽”。
所以不難看出,唐朝核心地區的官僚尚且沒有主觀意願上的做到對治下了如指掌,何況是邊陲新得未穩之地?
然而“忠義社”卻不同,社中子弟的父輩可能并沒有追求這些邊角料數據的意願,但是處在社中,作為非嫡長子或者庶出之流的人物,他們倘若有些雄心壯志的,便要在分家之時,能夠有足夠多的安身立命之本。
換而言之,他們需要錢,于是有了維持“忠義社”逐利的意願。而同時,張德在讓他們逐利的過程中,将過程原原本本地鋪展開來,每一個環節讓他們了解、旁觀、參與乃至組織。
數年來的潛移默化,即便是最愚蠢的二世祖,也知道這些環節“缺一不可”。
比如白糖,在賺取中國利潤的同時,他們回去向賈飛打聽,哪裡還能大批量種植甘蔗,如果有,那裡的自然災害是否頻發,如果頻發,減産後的收益能不能依然保本。他們找到了一塊新的甘蔗種植地,然後他們發現缺少足夠的勞力去種植,因為水土不服,有些倭奴無法适應熱帶的氣候,很快就病死了。
于是他們會去向巢氏打聽,黃蒿湯針對痢疾是不是真的有效,南人是不是要更加适合潮濕悶熱的熱帶氣候。
接着他們會去向王萬歲打聽,在嶺南的蠻族人口有多少,其中對中國“心懷怨恨”的是哪幾個。
然後他們會去向張綠水及麥氏子弟建議,把近海的船分撥一批到嶺南,接着就會安排“镖局”的镖師看押财貨,很快就會有“心懷怨恨”的蠻族份子前來襲擊,接着他們會高舉義旗,将這些“以下犯上”的部族消滅。
在此之後,他們會從孔穎達那裡得到教育,于是心靈得到洗滌的他們,不會殺死以及用皇帝的名義殺死這些俘虜。這些俘虜會活下來,用他們的勞動換取極少的自由。在那一年的賬單上,這些俘虜是他們的财産。
最後,一個嶄新的甘蔗種植園,誕生了。
這一切并非是結束,卻僅僅是一個開始。他們會找到張德,詢問有沒有更快的船抵達南海;詢問有沒有更安全的航線前往南天竺、高達國、獅子國、波斯國;詢問這一年的分紅利潤,可不可以全部轉為華潤銀元;詢問在洛陽北城置辦物業,大概需要多少華潤銀元。
青澀可愛的菜鳥們,不經意間,可能并非是像他們父輩期望的那樣,長成萬裡鲲鵬或者高志鴻鹄。他們有的像夜枭,躲藏在林子裡,發出奇怪的竊笑聲;有的失去了味覺也似,吃腐肉吃的飛起,成為了一隻秃鹫;有的成群結隊,每見屠城滅國便是嘎嘎興起,在光秃秃的樹杈上,冷冷地注視着千人萬人的死亡……
張德沒有告訴他們怎麼做,怎麼成長,十年來,老張從未幹涉過除少數幾人之外的任何成長變化。
這些不讨人喜歡的鳥兒們,卻自然而然地具備了超越唐朝地方主官的行動力,更是具備了超越外朝六部組織度的組織力。
當然,他們理所當然地還缺少點什麼,隻是,張德從來沒告訴過他們。
杜正倫離開漢陽的時候,是攥着幾份紅白雙契,有明年的白糖交易,有今年的新田開辟,還有木材交易、幹貨交易。
當然,杜正倫從張德這裡得到了一個确鑿的數據,黃豆和甘蔗是可以套種的,并且黃豆畝産情況優良的話,能達到三石。
這是一顆貼心丸,至少杜正倫可以放心去種甘蔗的同時,不用擔心餓死人。
“杜明理倒是走得快。”
碼頭上,李德勝笑呵呵地沖沙船揮手,然後扭頭看着張德,“不過操之,此人乃是幹才,拿他當王中的之流來糊弄,隻怕不成。”
“杜秀才是要做宰輔的人,歡州能呆幾年?”
張德笑了笑,不置可否。
“那可說不準,杜明理到底還是在太子左庶子位子上除職,倘使真有動搖國本的一天,難說杜明理會不會就縮在歡州不走了。”
李德勝這番話,讓二人不約而同地都有些皺眉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