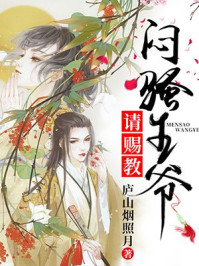額,超人?
曾紀澤一頭霧水,沒有聽過這個詞,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懵懵懂懂的點了半個頭,華皇的眼界,他已經很佩服了。
佩服的點在于,華皇看人準确,看事情客觀,很少帶有個人喜好,或者說,很少将個人喜好和工作混淆在一起。
萌總裁拍了拍巴掌。
王占奎即開門而入,“陛下。”
萌總裁對王占奎道:“把我每天看的兩本書拿過來。”
王占奎點頭答應,然後下去了。
曾紀澤好奇,不知道陛下要給自己看什麼書?
“我剛剛開始做皇帝的時候,内心是不安的,但是我現在這種不安的情緒,越來越少,活的越來越自信。”華皇笑着對曾紀澤道。
曾紀澤嗯了一聲,“陛下天縱奇才,這麼年輕就成就了曠古的功業,剛開始不安是因為還不熟悉,随着對全國的掌控越來越熟悉,便自然會安心了。”
華皇搖頭道:“這不是關鍵的地方,等會你看過我的兩本書,你就知道為什麼我越來越心安的原因了。”
曾紀澤哦了一聲,不知道是哪兩本書,會有這麼的力量?
王占奎不到一會就回來了,手裡面拿着兩本書。
曾紀澤一看書名,眼眶又紅了,眼淚就出來了。
華皇沒有要引曾紀澤哭的意思,是曾紀澤睹物傷情,因為兩本書的書名分别叫做《曾文正公日記》和《曾文正公家書》
後世有類似的作品,但都是後人整理的,肯定沒有華皇手中的這麼全面,這是統計局幫助整理的。
“你看一看,沒有什麼問題的話,這兩本書會放入華國中學生的課外閱讀書籍中。”萌總裁對曾紀澤笑道,“這個得征求你的同意。”
“陛下,這是對曾家的厚愛,我怎麼會不同意?多謝陛下。”曾紀澤從華皇手中接過兩本書,感覺沉甸甸的。
曾國藩的家書,共有上千封。
後世當然找不到這麼多,而且,這兩本書還是華皇親自參與編纂的,現在隻是樣本。
《曾文正公家書》全書分為治家類、修身類、勸學類、理财類、濟急類、交友類、用人類、行軍類、旅行類、雜務類,共10大類。
曾氏家族,向來治家極嚴,也很有章法。
曾國藩受家風熏陶,對子弟也要求極嚴,并諄諄加以教誨。
華皇認為曾國藩的家庭教育指導思想中,有許多可取之處。
諸如在教子弟讀書、做學問、勤勞、儉樸、自立、有恒、修身、作官等方面,都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自近代以來曾國藩就被政界人物奉為“官場楷模”。
他熟讀中國曆史,對官場之道參深悟透,積澱了一整套官場絕學,用之于中國官場,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曾國藩是最好的兒子,能使父母寬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導和照顧弟妹,體貼入微;曾國藩更是仁慈的父親,是兒女的好榜樣。
他的家書講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養,在骨肉親情日漸淡漠、鄰裡親戚形同陌路的現代社會裡,确實有勸世化俗的價值,值得每個人一讀。
曾國藩一生勤奮讀書,推崇儒家學說,講求經世緻用的實用主義,成為繼孔子、孟子、朱熹之後又一個“儒學大師”。
他革新桐城派的文學理論,其詩歌散文主持了道(光)、鹹(豐)、同(治)三朝的文壇,可謂“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曾國藩的家境還行,但是曾家絕不是什麼大地主家庭。
傳統時代,農民們想要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幾乎隻有供子弟讀書一途。
曾國藩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後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孫們靠讀書走出這片天地。
他不惜皿本,供長子曾麟書讀書,“窮年磨砺,期于有成”。
然而,曾麟書資質實在太差,雖然在父親的嚴厲督責下,兀日窮年,攻讀不懈,卻連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敗了。
作為長孫,曾國藩身上背負着上兩代的希望。
然而曾家的遺傳似乎确實不高明,曾國藩從十四歲起參加縣試,也是榜榜落第,接連七次都名落孫山(曾國藩的四個弟弟也沒有一個讀書成功)。
曾家已經習慣了考試失敗後的沮喪氣氛,他們幾乎要認命了。
然而,二十三歲那年,曾國藩的命運之路突然峰回路轉。
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舉人。
又五年之後的道光十八年,二十八歲的曾國藩中了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剛過而立之年的曾國藩和每個普通人一樣,有着大大小小許多缺點。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
曾國藩天生樂于交往、喜歡熱鬧,诙諧幽默。
在北京頭兩年,他用于社交時間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東家串西家,酒食宴飲,窮侃雄談,下棋聽戲。
雖然他給自己訂了自修課程表,但執行得并不好,認真讀書時間太少,有時間讀書心也靜不下來。
“我完整的看過曾國藩日記。”華皇對曾紀澤道。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國藩在日記中說,四月份“留館”之後,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他總結自己四十多天内,除了給家裡寫過幾封信,給人作了一首壽文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
因此,他在日記中給自己立了日課,每天都要早起,寫大字一百,溫習經書,閱讀史籍,還要寫詩作文。
翻開日記,責備自己“宴起”、“無恒”、“太愛出門”的記載到處都是。
二是為人傲慢,修養不佳。
雖然資質并不特别優異,但曾國藩在湖南鄉下朋友裡總算出類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顧盼自雄。
在離家到京服官之際,他那位識字不多卻深有識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給他這樣的臨别贈言:“爾的才是好的,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當然不足以掃平他身上的處處鋒芒。
在北京的最初幾年,“高已卑人”,“凡事見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這最常見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體現得很明顯,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處甚多。他的幾個至交都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傲慢”。
他的好朋友陳源兖就告訴他:“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又言我處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第二個是“自是”,聽不進不同意見,“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
因為修養不佳,脾氣火爆,曾國藩到北京頭幾年與朋友打過兩次大架。第一次是與同鄉、刑部主事鄭小珊因一言不合,惡言相向,“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于忘身及親”。另一次是同年兼同鄉金藻因小故口角,“大發忿不可遏,……雖經友人理谕,猶複肆口謾罵,比時絕無忌憚”。這幾句描寫形象地描繪了曾國藩性格中暴烈沖動的一面。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錯誤是言不由衷,語涉虛僞。比如在社交場合常順情說好話,習慣給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誇,不懂裝懂,顯擺自己,誇誇其談。人性中這些常态在曾國藩身上一樣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個缺點就是“僞,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
在曾國藩日記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這個缺點。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雲來拜訪,“示以近作詩。贊歎有不由衷語,談詩妄作深語”。贊歎之辭并非發自内心。而且聊着聊着,自己就故意顯擺高深,誇誇其談起來。這樣的記載數不勝數。
席間,面谀人,有要譽的意思,語多諧谑,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
對于一般人來說,這是無傷大雅的社交習态,如同喝湯時不小心會出聲一樣,幾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對于聖人之徒來說,卻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因為儒家認為,修身之本在于“誠”。對自己真誠,對别人真誠,一是一,二是二,一絲不苟,才能使自己純粹堅定。适當的“善意謊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但當言不由衷成為習慣時,“浮僞”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變得庸俗可憎。
三十歲是曾國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嶺。
曾國藩之于後人的最大意義是,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一個中人,通過“陶冶變化”,可以成為超人。
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真誠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領可以增長十倍,見識可以高明十倍,心兇可以擴展十倍,氣質可以純淨十倍。愚鈍之人,通過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說得出,辦得來。浮嚣之人,也可以變得清風朗月般從容澄靜。偏執之人,亦可以做到心兇開闊,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為官,不僅是曾國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個重要起點。
作為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當時最頂級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淵薮。
一入翰苑,曾國藩見到的多是氣質不俗之士,往來揖讓,每每領略到清風逸氣。
曾國藩發現,這些人的精神氣質與以前的朋友們大有不同。他們都是理學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熱情。他們自我要求嚴厲峻烈,對待他人真誠嚴肅,面對滾滾紅塵内心堅定。
三十歲前的曾國藩人生目标隻是功名富貴、光宗耀祖。結識了這些良友之後,檢讨自己,不覺自慚形穢,毅然立志。
正是在三十年這一年,曾國藩立下了“學作聖人”之志。
“聖人”是儒學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标。
人類最基本的一種心理傾向就是使自己變得完美。
中國儒、釋、道三家,對生命目标的設計都是極其超絕完美的。
道家以為,人通過修煉,可以不食五谷,吸風飲露,逍遙無恃,長生久視,與天地同,成為“至人”、“真人”、“神人”。
超自然的誇張固然過于虛幻,不過,除去這些飄渺的因素,儒家的“聖人”理論畢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着符合人類基本心理經驗的合理内核。
“怎麼樣?還算是全面吧?”華皇問道。
曾紀澤點頭道:“很全面了,很多都是連我也沒有看過的。”
“嗯,我讓人搜羅的。你還可以再補充一下。”萌總裁笑道:“專門讓人去找了祖父曆任師爺,本來還想弄個傳記,但是我想傳記就不要了。”
曾紀澤點點頭,明白華皇的意思,陛下是欣賞父親的做人,律己,這些方面,但是對父親整個人生,尤其是後半段在清廷的發迹經曆,還是有所保留的。
不過,華皇能這麼推崇父親,已經讓曾紀澤很感動了。
“在想不通該怎麼做事的時候,看看。”華皇笑着對曾紀澤道,“沒有什麼事情是解決不了的。記住,對德國人,或者說對所有的列強,我們都沒有必要放低姿态!”
曾紀澤點點頭,眼睛一亮,陛下終于說到讓他去德國出訪的事情了。
“你到了德國之後,多和各方面接觸,不急于和俾斯麥接觸,到時候,我會親自和他談。當然,如果他主動召見你,你可以和他談一談。德國,奧匈帝國,這些在海洋上的後起之秀,都是我們可以優先選擇的盟友,因為暫時和我們沒有多少利益沖突。”萌總裁直接指示道。
“好的,陛下!”曾紀澤暗道,這些事情我都知道的,隻是怕德奧對我們不重視,根本不理睬我們,怎麼辦?不過,曾紀澤沒有将這個疑問問出來,作為外交大臣,這種問題也要問陛下的話,還要他做什麼?
曾紀澤欲言又止,華皇也是同樣,曾紀澤比李鴻章年輕的多,而且和自己的關系近的多,在原本的曆史中,曾紀澤因為生病,年紀輕輕就死了,現在是華國時代了,華國的醫療水平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