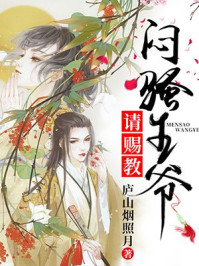軒洪濤居然被軒悅萌的目光逼視的有點兒心虛,意動之餘,他的确有些不敢去,雖然自己家的老頭也是個正三品,但是他見過的最大的官就是自己家的老頭和崇厚,崇厚的排場是很足的,架子也是很大的,而且他跟直隸總督李鴻章連見都沒有見過,等下别大功沒有立,先被人打一頓。
須知侯門深似海啊!
軒洪濤怔怔的看着軒悅萌,又四下到處看,眼神飄忽不定,就是不說去。
軒悅萌暗自歎口氣,尼瑪,我一個幾個月的人都不怕,你活了三十多歲怕個毛啊,“去不去,給句痛快話吧!你活這輩子就賭這一把大的了,你敢不敢?”
賭這個字激發了軒洪濤,“你到底看不看的懂洋文?這上面真的說的是法國打仗的事情?别到時候弄個大罪在身上。還有,你幹什麼不直接喊老爺子去,他要見總督的話,比我容易的多。”
軒悅萌白了軒洪濤一眼,“他容易立大功,沒錯,軒宗露是比你容易立下這個功勞,但是他立了大功的話,跟你連個屁的關系都沒有!到時候他加官進爵,好處都讓軒洪波撈去了!跟我就更沒有屁的關系啦!你到底敢不敢去的吧?給句痛快話。”
軒悅萌的思路清晰,說服力強,一句一句都擊中軒洪濤心中的軟處,忽然覺得自己面前人小鬼大的軒悅萌像是個妖怪轉世,不過,縱使這孩子是妖怪,那也是我的孩子,是向着我的妖怪,猛的下了決心,猛的一咬牙,一跺腳,将軒悅萌抱起來遞給大智抱着,“去就去!就賭這一把!”
軒悅萌大汗,看軒洪濤的意思,你這不是去報信,這是去上沙場打鬼子呢?
大智也覺得好笑,很難得看見軒洪濤有這麼果斷的時候。
三個人趁夜色來到了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這裡原先是崇厚的衙門,不過出了天津教案之後,崇厚就赴京去了,一直沒回來,現在已經成了李鴻章的行轅。
到了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口,軒洪濤又害怕起來,“要不然,你還是讓你爺爺去吧。”
軒悅萌大汗,示意軒大智抱着自己過去,對着守門的親兵頭領朗聲道:“快給我們通傳,我爹是天津機械制造局的管事軒洪濤,我們有關于對法國談判的重要隐秘要告知李中堂!”
親兵頭領同樣被軒悅萌吓了一跳,看上去就是個不滿一歲的小孩,怎麼可以這麼有派頭?而且一個小屁孩說話說的這麼清楚?看了一眼在台階下站着的軒洪濤,是個人一看軒洪濤那畏畏縮縮的樣子和服裝,就知道軒洪濤不是官身,一個制造局的管事?什麼玩意,老子好歹是官,你個管事算個屁,臭蟲般的人也敢跑總督行轅來求見總督大人啦?“一邊去一邊去,這麼小個小孩就這麼不懂規矩,中堂是想見就能見的?小孩不懂規矩,大人也不懂規矩嗎?想見中堂,明日到衙門找幕事房的師爺們,說明緣由,等着聽信,然後等着安排接見。”
軒悅萌冷笑一聲,“我們可以等到明天,但是恐怕是李中堂等不了明天,你剛才沒有聽見是關于法國人的重要隐秘要上告李中堂嗎?你們這不知道這法國人是怎麼回事?有大炮軍艦的洋鬼子要把天津城都夷為平地啦呢!事關緊急,到了明天耽誤了朝廷的大事,你全家的腦袋砍了也不夠定罪,别說是你們啦,到時候恐怕連李中堂自己也吃罪不起!”
其實軒悅萌自己也知道想見李鴻章不容易,這是中央級别的大員啊,要是在後世,别說見中央級别的官,想見個縣長都不容易!别說縣長,想見個校長都不容易!軒悅萌上輩子見過的最大的官,就是大學裡面的教導處主任。那還是因為晚上和女同學在操場抱着親嘴,被學生會查夜的給逮住了。
果然,親兵頭領被軒悅萌逗笑了,“喲呵,您這位小爺是王八小口氣大!再不退下,以滋擾總督行轅的大罪把你們都關起來。”
軒洪濤吓了一跳,就要上去将軒悅萌抱走,軒悅萌卻并沒有這個兵頭給吓住,還沒有等軒洪濤上前,接着道:“大人,我不是故意難為你,确實是十萬火急,實不相瞞,我爺爺正是這三口通商大臣衙門的總辦章京軒宗露,這衙門我原先一天進出無數次,咱們都是大清的子民,當此國難臨近之際,更當不顧個人得失的為國家盡力,我看大人你一副福相,面帶忠直,定然是位為國為民的好大人,麻煩你現在就往裡面通秉一聲,事情不成,跟大人沒有什麼瓜葛,事情如果真的緊急,自然有人讓我們進去,到時候見了李中堂,我父親絕不會忘記向中堂大人陳述大人你當值的時候盡忠職守的事情。”
親兵頭領被軒悅萌微微的有些說動,其實報不報的,跟他并沒有什麼關系,他本來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想趕緊将人打發走,被軒悅萌一頓各種角度的遊說之後,笑道:“小屁孩子一套一套的,諾,是你們自己不知輕重,可别怪我沒有提醒你們,衙門裡面的大人脾氣可一個個都比我大,你們等着!”
軒悅萌一見這人肯去通傳,大為開心,小胖爪子舉了舉,“多謝大人。”
那人主要倒不是怕軒悅萌說的什麼事情急,事情急不急的關他屁事,主要軒悅萌左一口大人右一口大人的,說的他高興,不然連通傳費都沒有一文,誰願意跑來跑去?
軒悅萌的運氣不壞,李鴻章正在同身邊的親近幕僚盛宣懷商議同法國人談判的事情,曾國藩沒有撈到好下場,他的日子也不好過,連日來與法國人的談判,已經使得李鴻章焦頭爛額。
“中堂,朝廷的意思,最多賠四十萬兩,法國人卻要一百萬兩,而且要将天津一應官員當即正法,氣焰實在是太嚣張了,幹脆就照着清流們的意思,談崩了得了!省的大人您落個兩頭不讨好,這趟差事真的燙手的山芋。”盛宣懷精明能幹,是李鴻章的心腹幕僚,李鴻章的對外事務和絕大部分的商業事務都是由盛宣懷幫助處理的。
李鴻章已經洗過腳,正由仆人在給他擦腳穿襪子,李鴻章理了理頭發,“杏荪呐,我何嘗想跟法國人談,談崩了?談崩了隻能是讓生靈塗炭,來的一路上你沒有看見嗎?法**艦已經雲集口外,随時準備對我開戰呐!咱們打的過人家的洋槍洋炮嗎?搞洋務,絕不能意氣用事,我聽那法國公使羅書亞已經有松口的意思,我打算跟他談到賠償五十萬兩,盡量保全天津的官員,能免于死刑便可,隻要先免于死刑,将來再想法一個個給保回來,就走個過場,這個條件,相信朝廷也能夠答應的。如果在我的手裡給法國人以開戰的口實,我們就将會成為千古罪人呐。列強,不可欺也。”
盛宣懷點點頭,“是啊,賠償四十萬兩總歸是可能性不大,曾老相爺上來就賠了法國以外的各國四十六萬兩,法國在這次教案中是損失最大的,怎麼樣也不會同意低于這個數。”
李鴻章歎口氣,閉上眼睛,他要思謀着明天對法國領事的談判,這場拉鋸戰把他折騰的夠嗆。
盛宣懷下面的幕僚已經被門官通傳了,低階幕僚再報中階幕僚,再去見了大門外的軒悅萌三人,那中階幕僚拿來了一份軒悅萌給的報紙,在門外探了探頭,見盛宣懷正跟中堂大人在談事,便不敢打擾。
這中階幕僚覺得事關重大,又查明了軒洪濤确實是天津機械制造局的管事的身份,便不敢耽擱,徑直來到了李鴻章的寝房外。
幕僚之所以敢在這麼晚來找,一方面是因為李鴻章的架子并不大,對手下人都很寬容,另一方面是軒悅萌說的頭頭是道,雖然是從一個小孩的口中說出來,卻很讓人信服,而且這洋報紙也加重了軒悅萌說話的分量。
盛宣懷看見了下屬,見李鴻章正閉着眼想事情,便悄聲出來,“什麼事?”
那幕僚将報紙遞給盛宣懷,“大人,這是大門外一對想要求見相爺的父子拿來的,他們說掌握了法國人的重要信息,是有關天津教案的談判的,想見見相爺。”
盛宣懷皺了皺眉頭,拿過報紙一看,“都是洋文?寫的什麼東西?你頭一天當差啊?這都什麼時辰了?相爺是說見就見的啊?他們當自己是誰啊?下去!”
幕僚不知道該怎麼作答,正要退下,又被盛宣懷給攔住了,“來的人有無官職?”
幕僚:“是天津機械制造局的管事,沒有官身。”
盛宣懷笑了,“想巴結都想瘋了吧?一個沒有官身的也想見相爺?你去回了他們吧!”
李鴻章聽見了外面的動靜,“杏荪,什麼事情?”
盛宣懷見驚動了中堂,不得不将幕僚對自己說的事情簡單說了一遍,“相爺,這種人常有,這洋人的事情,他們懂多少?都是想立功想瘋了的人。”
李鴻章拿過那報紙來看,“天津機械制造局的人?能拿洋報紙來,至少認得洋文,這樣的人總歸算是我大清國不可多得的人才,讓他們進來吧。”
軒悅萌,軒洪濤,軒大智三人在大門外已經等了許久了,軒洪濤後悔不已,幾次想走。
“算了,不見就不見吧。”軒洪濤抱起軒悅萌。
軒悅萌:“我無所謂,不過我剛才已經将你的名字都報給人家了,你如果不等,到時候萬一李大人真的要見你,而你又跑走了的話,你就是故意戲耍中堂的罪過。”
軒洪濤被軒悅萌吓了一跳,又将軒悅萌給放了下來,連連的在原地跺腳,“這次真的被你害死了!我也真的是糊塗了,我怎麼會聽你一個剛斷奶的小屁孩的話?你可把我給害苦了!你你你!你把全家都害苦啦!”
軒洪濤焦急的左手挫着右手,一個勁的往裡張望,既希望有人出來又怕有人出來,猛的見到剛才那幕僚從裡面走出來,驚得渾身發燥,恨不得拔腿往回跑,想到有可能要見到李鴻章這麼位高權重又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就覺得有些呼吸困難。
幕僚出來了,對着軒洪濤道:“跟我來吧,你一個人進來就行。”
其實軒悅萌對于能不能見到李鴻章并不感興趣,或者說對于才八個月大的他來說,見不見都一樣,他反正是不能當官,軒悅萌主要是要讓軒洪濤獲得一次機會,能夠改變現在的困逆處境的機會。
軒洪濤看了看軒悅萌,忽然覺得沒有軒悅萌在就一點安全感都沒有,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的道:“大人,這些都是小兒發現的,他可能說的更加清楚些。”
那幕僚雖然剛才很驚訝于軒悅萌這麼小的一個小孩就可以說話說的這麼好,卻沒有想到在這對父子當中,原來這小不點兒才是主心骨,也頗為瞧不起這父親,甚至有些後悔進去替他們通傳了,覺得這身帶酒味的畏縮男人很不靠譜,“那你們一起進來吧,懂規矩吧?别在相爺跟前亂講話啊。”
軒洪濤忙不疊的從軒大智手上将軒悅萌抱過來,“謝謝大人,我懂規矩的,絕不敢在相爺面前亂說什麼。”
到了這一刻,其實軒洪濤的酒是早被吓醒了,兩隻眼睛充着皿絲,整個人異常的亢奮,跟個貓頭鷹差不多。
就這樣,軒悅萌沒有想到他重生沒有多久,便可以見到曆史上赫赫有名的李鴻章,當然也頗為激動,他對李鴻章并沒有什麼了解,這名字卻是熟悉的很的,軒悅萌就知道似乎晚清的最後這三十來年的曆史就是李鴻章和慈禧兩個人的曆史。
軒洪濤一路跟着那幕僚往内走,抱着軒悅萌的手都有些打抖了,也不知道是因為緊張還是因為饑餓,畢竟有好長一段時間,大房都隻能過一天吃一頓稀飯的日子,那還是因為老婆怕他出去賭,等他那最近的一次月俸銀貼拿回家,立刻就全部換成了糧食,現在糧食都用光了,家裡已經在靠典當過日子了。
軒悅萌反而平靜了下來,李鴻章也好,慈禧也好,對于他來說,并沒有什麼大的感觸,似乎對于現在的生活,他都還有些沒有完全融入,如果是在現代見一個地委書記,可能軒悅萌都要比現在激動一點的,李鴻章究竟有多大的權力和聲望,他直到這一刻都還并沒有一個明确的概念。
李鴻章這時候才四十**歲,須發都還是黑色的,跟軒悅萌以前在電視裡面看見的凡是有李鴻章這角色就是一個六七十歲的白發蒼蒼的幹巴瘦小老頭的印象差很多,而且李鴻章還長得頗為富态,方面大耳紅光滿面的,隻是略微有些憔悴,李鴻章居然真的在夜裡召見他們父子,光憑這點,其實李鴻章在軒悅萌心中的印象已經大加分了!
李鴻章的聲音很有中氣,音量不大,卻很沉穩,都在一個音階上面,不疾不徐的:“你找本堂有何事?”
李鴻章僅僅是一句話,簡單的幾個字而已,一股極其強大的官威便撲面而來,軒悅萌終于明白啥才叫一品大員,啥才叫不怒自威,這份風采,啧啧。
軒悅萌瞪着他那烏黑溜溜的眼珠仔細看李鴻章。
軒洪濤将軒悅萌放在了地上,給李鴻章行了讀書人的禮節,咽了口口水,居然發不出聲音,壓着嗓子咳嗽一聲,“回……回中堂的話……嗝……嗝……”
軒洪濤說完這五個字居然不記得該說什麼了,居然還打起嗝來!
尼瑪,軒悅萌差點氣出屎來,真的是狗肉上不了酒席,您能有點出息嗎?這是哪裡啊?你在這裡打嗝?有這麼緊張麼?
軒悅萌忍不住了,接着道:“中堂大人你好,我父親得知中堂大人正和法國人為了天津教案在談判,憂心國事之餘,因此對法國的動向便多加留心,在租界收集到一些關于法國人的信息,覺得對中堂大人的談判可能有用處,便急着給中堂大人送來啦。”
李鴻章點點頭,顯然也很好奇于軒悅萌這麼一個小孩居然可以表達的這麼清晰,本來還對于大人居然帶着一個小孩子來見自己而有些奇怪的,不由的眯眼微笑,對着軒悅萌道:“那你爹爹會洋文?”
軒悅萌看了軒洪濤一眼,軒洪濤先生已經吓得在輕微的打擺子了,一副連站都快要站不穩啦的架勢。
軒悅萌沖着李鴻章點點頭,朗聲回答道:“我父親看見中堂大人有些緊張,他懂一點洋文,我也懂一點洋文,我的洋文都是我爹教我哒。”
軒洪濤吓了一跳,我懂狗屁洋文?你一個小屁孩,你又懂狗屁洋文啊?這裡是可以吹牛的地方嗎?你跟你二叔真不愧是一個家族的啊!這是遺傳嗎?
軒洪濤不知道李鴻章懂不懂洋文,生怕李鴻章等下忽然用洋文跟他父子來上兩句對話就要崩了,暗暗叫苦不疊。
李鴻章聽軒悅萌說的話居然跟一個小大人一般,雖然内容很正常,不過想着自己正跟一個這麼大點兒的孩子交談,也覺得有趣,對着軒悅萌招招手,示意軒悅萌到他的身邊去,等到軒悅萌晃晃悠悠的過去,握住了軒悅萌的小胖爪子,“那你能不能跟我說說看,你這報紙上面,講了法國的什麼内容啊?”
軒悅萌哦了一聲,從懷中的小兜兜内又拿出四份紙頭,連同李鴻章身邊的那份,放在一起講解道:“中堂大人請看,這兩份是報紙,這兩份報紙一份是英國人的報紙,一份是美國人的報紙,在這個地方,這個地方,都有提到法國人的文章,說法國正在同普魯士進行大的戰争,而且英國人的報紙明确的指出了法國人現在正處于劣勢。”
軒悅萌用手指着,說完也不客氣,“你們拿一隻筆來,我給您圈出來吧,說法國人戰争劣勢的是這句,這兩篇文章分别在這裡。”
盛宣懷急忙從旁邊桌上給軒悅萌取來一直蘸了墨汁的毛筆,軒悅萌分别把剛才講的地方都畫了出來。
軒悅萌見李鴻章聽的津津有味,便繼續道:“這三篇是洋人商人們用過的便箋,都有提到普法戰争,商人們對于戰争是最敏感的,國家強盛,則法郎增值,國家衰落,則法郎貶值的厲害,這三篇便箋上面都提到了法郎貶值的事兒,而且都認為法郎還将在最近幾年持續大貶值!這些都充分說明了,這次的普法戰争,會讓法國人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霸權都受到動搖,法國在近五年内想對我大清作戰都不可能,如果我估計的沒有錯的話,天津口外的法軍軍艦應該早在一個月前就全部悄悄撤離了,中堂知道了這些信息,在和法國人談判的時候,當能握有主動權。”
軒悅萌說的高興,索性将心裡想的事情全都說出來了,也懶得再去顧及要不要隐藏一點實力的事情,雖然他很厭煩滿清,但是畢竟現在滿清就代表着中國,他還是有愛國熱情的,當然不希望國家的錢稀裡糊塗的一直往西洋帝國主義那邊流。
李鴻章像是看着一個寶貝般看着軒悅萌,已經被眼前這小不點給驚呆了,這還是一個小孩嗎?簡直是一個妖怪吧?震驚了一會,不由的看向軒洪濤,“這是你兒子?他多大了?他說的都是對的嗎?”
軒洪濤的注意力都在李鴻章身上,見中堂問自己,連忙點頭,點頭點的那叫一個機械化,像是個機器人一般,軒洪濤哪裡說的出話來,又死勁咽了一口口水,才道:“是的,中堂……大人,犬子八個月大了,犬子說的都是我想說的。”
李鴻章撫掌哈哈大笑,“杏荪,誰說我大清缺人才?一個八個月的小兒就有如此的智慧和才華,天縱奇才啊!好,好,好!”
李鴻章連說了三個好字,盛宣懷也親自給軒悅萌斟了一杯茶過來,“孩子,說了半天,喝點水吧,相爺誇你了呢。”
軒悅萌萌萌哒的笑笑,喝了一口水,趴在了李鴻章的腿上。
任務算是完成了,不管成與不成,也不管結局如何,軒悅萌忽然覺得一陣輕松,整個人也忽然覺得很疲憊,他畢竟還隻是一個八個月大的小人,今天有些超負荷工作了。
軒洪濤正要阻攔,李鴻章笑着抱起來軒悅萌,“我的一個小女兒比這孩子還大上三四歲,到現在都還說不出完整的話呢,你這孩子他叫什麼名字?”
軒洪濤連忙答道:“回中堂的話,這孩子叫做軒悅萌,字雨堂。”
李鴻章重複了一遍軒悅萌的名字和字,捏了捏軒悅萌的小胖爪子,兩隻手在軒悅萌的胖嘟嘟的臉蛋上捂了捂,“雨堂,軒悅萌,軒雨堂,好啊,好名字,你是在天津機械制造局當差?什麼職司?有無品級?”
軒洪濤:“回中堂的話,小人是在天津機械制造局當差,帳房做個普通管事,沒有官身。”
李鴻章點點頭,“崇厚大人回京去了,聽說天津機械制造局已經停了有一陣日子了,我都沒有顧得上來那頭的事情,這樣,你明天來找這位盛宣懷大人,你先幫着盛大人讓天津機械制造局重新動起來,好不好?”
軒洪濤大喜過望,他不傻,雖然李中堂沒有承諾什麼,這對他來說已經夠了,至少有兩點,第一,李大人這下就算是認識自己了,還給自己派遣了差事,那麼從此自己就是李大人的人了!那麼他們大房這邊應該就此平安了,就算老爹還沒有完全脫離危險,他自己這一房也應該算是平安無事了。第二,李大人讓盛大人先主持天津機械制造局的事情,那麼肯定是要大換皿了,到時候自己也算是元老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嘛,機會真的來了!軒洪濤急忙連連謝恩。
李鴻章對軒洪濤的印象也不錯,雖然軒洪濤的話不多,形象也差了些,但是言談上也還算是得體,最關鍵兒子都這麼天才了,天才的老子也不該差太多吧?
李鴻章認為軒洪濤是個有才之人,大抵的有才之人,都是不修邊幅的,這些細節上,更加深了李鴻章對軒洪濤有才這點的印象。
軒洪濤怎麼也不會知道自己邋裡邋遢的扮相,居然能夠入了李中堂的法眼,居然還成為了優點啦。
李鴻章再跟軒洪濤随意的話了話家常,幾句話便将軒洪濤的家世背景弄得清清楚楚,這才讓軒家父子離去。
來的時候,軒洪濤的手在抖,回去的時候,軒洪濤的手似乎抖的更厲害了,隻不過心情截然不同!來的時候是緊張,去的時候是高興,是興奮,是一種即将要騰龍四海的豪情壯志,雖然仍然饑餓,抱着軒悅萌卻走的騰騰騰的很有勁。
“無風三尺浪,平步起青雲啊啊啊啊啊……”
嘿!軒洪濤還偷偷的哼上了老戲啦。
軒悅萌心中暗笑軒洪濤,但是他并不是很樂觀,就是剛才李鴻章那最後幾句側面打聽軒洪濤家世的話,讓軒悅萌有點不安,軒宗露如果從曾國藩的這方面算上來,應該算是跟李鴻章有些淵源,可以歸為湘軍大系統的,但是軒宗露八面玲珑,還有李鴻藻那邊的背景呢,也不知道李鴻章會不會接納軒洪濤,畢竟這以後,直隸地面應該都是李鴻章說了算了。
不過這些擔心,軒悅萌也沒有去跟軒洪濤說,一方面是他覺得沒有什麼必要,順其自然的比較好,另一方面是即便跟軒洪濤說了,軒洪濤也同樣沒有什麼辦法去改變李鴻章的想法,還會增加軒洪濤的擔心,減少軒洪濤現在的快樂,軒洪濤的心情好了,大房那邊的日子應該能順心一些的吧?
軒洪濤忽然停下哼哼老戲,深深的看了軒悅萌一眼,傻樂一下,又猛的在軒悅萌的臉上親了一口,“嗯,以後别回大宅了,晚上讓你跟你媽睡!”
軒悅萌大汗,神經病!
軒洪濤想了想,又道:“晚上還是要回去,大宅那邊吃的比較好,等爹發了月俸再跟老爺子說說,把你接過來跟我們住!”
軒悅萌:“我不是已經過繼給四房了?我要搬過去也不能是一個人吧?”
軒洪濤這才想起軒徐氏來,“房子是不夠,那等爹攢夠了錢,換個大院子,到時候比大宅還要大!到時候讓四房一起過來!”
軒悅萌:“四房跟大房一起住?怎麼可能啊?有哪家弟媳婦跟大伯住一起的?”
軒洪濤:“……”
軒悅萌:“那你也可以努力存錢,買院子的時候多買一個,讓四房也可以分出來過。”
軒洪濤:“……”
軒大智很驚訝于軒洪濤對軒悅萌的态度轉變這麼大這麼快,回去的路上,軒洪濤居然一直堅持要親自抱着軒悅萌,直到累的不行了才給軒大智。
“大爺,怎麼樣?事情辦的很順利吧?”軒大智問道。
軒洪濤咳嗽一聲:“大智,過一陣子,我就跟老爺子說說,等我買個院子,再把悅萌接出來住的時候,讓你一起過來,以後你就是悅萌的貼身仆人,你可願意?”
軒大智一陣高興,“大爺,願意的。”
不過大智轉念一想,你一家人連飯都吃不飽,等你買院子?唉……準是又想着從哪裡弄錢去賭博了。
軒家父子這邊一走,李鴻章連忙讓盛宣懷連夜去找通譯将軒悅萌拿來的五張紙頭都譯出來,通譯的水平肯定比軒悅萌差遠了,不過大概的意思還是可以弄明白的,李鴻章确認了軒悅萌給出的信息的真實性之後,再派人立刻快馬去天津口外,六百裡加急沿岸勘察,看看法**艦的動向。
李鴻章想想剛才軒悅萌說話的樣子就好笑,才隔了很短暫的時間,他發覺自己居然就有點想剛才那個人小鬼大的小孩,李鴻章實在猜不透老天造人怎麼可以如此神奇,居然能造出如此天才的小兒,曹植七步成詩的時候也十多歲啦啊,這小兒才八個月啊,就可以參與軍國大事了,比曹植可厲害多了,比任何一個天才都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