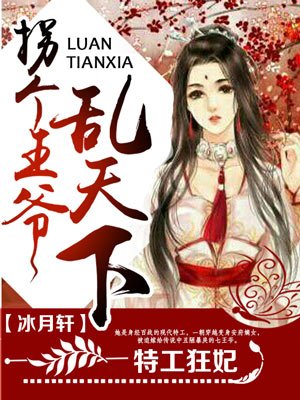倉庫裡很安靜,其他人面面相觑的搞不清楚這局勢,隻等着看這父女倆最終會給出一個怎樣的結果。
盛叔有幾秒沒有說話,那雙眼睛很溫和,卻又不失吞噬一切的暗芒。
“可以。”
他擡手一擺,“出去。”
淡淡的兩個字,沒有人敢忤逆。
有手下上前去關好另一扇門,那些被套着黑色頭套的“貨”被隔絕在另一個空間,随後包括喵爺在内的其他人全都退了出去。
這偌大的倉庫,頓時就隻剩下對向而站的父女,和昏迷的男人。
“想跟爸爸談什麼?”
“我……”
姜也眼眸通紅,有被風霜浸洗過的瑩亮,但并沒有淚。
她暗自沉了口氣才掀起眼皮,嗓音沉啞,“您雖然是我的父親,您知曉我的一切,我對您卻是一無所知,你不覺得這樣很不公平麼?”
付銘盛眉眼微微落下,歎息道:“是爸爸的錯。”
這樣的語調,仿佛有種沁人心脾的舒适。
“所以小小,你有什麼要求都可以提,我會盡我所能的補償你。”
他思索片刻擡腳走過來,帶着玉扳指的那隻手摸着她的頭發,“你媽媽離開以後,我就沒有過别的女人,你們三兄妹裡爸爸最喜歡的是你,虧欠最多的也是你,留在爸爸身邊吧。”
姜也看着眼前這張和自己有三分相像的臉,那雙黑色的眸子裡浮動着如山的父愛,分不清真假。
父愛?
很久違。
久違到陌生。
她隻看了付銘盛兩秒,然後就再次被後方的男人吸引了視線,心口忽然一窒,仿佛有來自深海的壓力朝她湧過來,痛到難以呼吸。
“我不知道。”
姜也難耐的閉上眼睛,幾乎用盡全部力氣。
“您很清楚我來這裡的目的不單純,我本來是想為我哥哥報仇,也就是……當年救了我的人,他死了……”
她聲音梗了一下,整張臉都處于緊繃裡。
繼續。
“我查到是袁老殺了他,所以才設計了一切,包括他——”
鐵籠裡的男人依舊毫無生息,垂着頭,精緻的五官處于半明半暗的光線裡,好像一個支離破碎的标本。
姜也背心裡冷汗涔涔,視線有種近乎炫白的模糊,可她還是能清楚的看到他,于是更加知道自己沒有退路。
指甲深深地掐進掌心裡。
她問出口:“您應該知道我跟他有過一段吧。”
“當然。”
付銘盛同樣轉過去看向許溫延,語氣竟然帶着惋惜,“小小,爸爸知道你當初跟他在一起是有原因的,他對你也不是很好,你想要殺了他還是想留下他,我都可以答應你。”
一個人成功的要素就在這裡,不拘泥于小節,隻要結果是走向自己設定的大方向,其他不重要。
可以是敵人。
也可以是自己人。
窗外很遠的地方有海浪拍打着礁石,聽不見聲音,但那狂浪陰霾的形态就令人心生膽怯。
姜也定定的站着,清冷的面容沒有任何表情,像極了曆經情感波折的漠然女人,“我留下,放他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