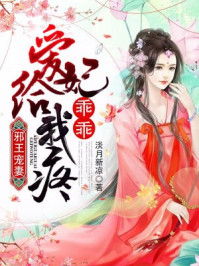牡丹花太後笑眯眯親自打簾,帳門一掀,頓時就看見了正對帳門的窄谷出口。
那裡,彌漫硝煙裡,正不斷滾落黑色的山石,出口已經被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塊填平,山上還有石塊不斷落下,将底下那些護衛打得到處亂竄,驚呼聲慘叫聲亂成一團。
“我們沒做什麼。”劉牡丹謙虛的道,“也就是炸了一小段山,把這個出口給堵住而已。”
弘吉勒張着嘴,看着山石高壘的入口,一時已經忘記說什麼,祿贊臉色死灰,此時赫連铮才将一直盯着他的目光收回,撣撣袍子,雲淡風輕的笑道:“現在,我夠不夠格和你們同歸于盡?”
“……”
帳篷裡此刻的沉默令人更加難熬,誰也沒想到赫連铮狠起來竟然完全的不顧後果,火藥炸山,堵死出口,将他自己和大家全部堵在這不能進出的窄谷裡,那擺出的架勢,真是你咬我一口,我滅你全家,生死不計,丢命拉倒。
之前隐約聽說他将貔貅部滅族,衆人還不相信,此時看這小子比狼還狠比豹子還烈的行事風格,才知一定不會有假,貔貅部族長提前趕來參盟,并不确定族中的事情,此刻臉上的神情,已經無法用言語形容。
赫連铮笑眯眯高踞座上,環顧四周,學着鳳知微的眼神,自己覺得很夫妻相。
“劄答闌!不要沖動!”沉默半晌後,庫爾查以叔父身份上前怒叱,“不要惹得不可收拾!我以族長身份命令你……”
赫連铮一偏頭,斜睨着他。
那目光看得庫爾查顫了顫,想好的一句話突然便卡在咽喉裡再也說不出口。
半晌赫連铮好奇的道:“你誰?”
“……”
庫爾查僵立在地,手和嘴唇一起都在顫抖,硬是抖不出一句完整話來,赫連铮卻已經一眼都不屑看他,高踞上座,垂下眼睛,慢悠悠的拭自己的腰刀,“劄答闌因爾吉的眼睛,隻看得見人,至于畜生……”
他一笑,搖搖頭。
“滿堂皆無人啊……”他仰首長歎,不勝惋惜。
滿堂“畜生”面無人色,連一直站在帳門附近堵住鳳知微,崩山都沒多看一眼,隻顧将她從頭到腳打量個遍的克烈,都目光微微一閃,回頭看了一眼。
不過他的目光很快拉回,皺着眉又望了鳳知微一眼,再次歎息:“醜,醜。”
鳳知微看都沒看他一眼,隻關注着赫連铮,聽見他那一句滿堂無人,不禁一笑,心想世子爺中原去了一趟,學了不少拐彎抹角的罵人本事。
克烈原本已經失望的轉開眼,看見這一笑眼前一亮,隻覺這黃臉女子一笑間婉轉雍容,迷蒙眼眸波光流轉,竟有常人難及的韻緻,不由贊道:“笑起來還像個美人……”伸手就去摸她的臉。
“啪。”
一枚黃呼呼的東西電射而出,雷霆般直奔克烈眉心,這麼小的東西,這麼短的距離,竟然射出呼嘯猛烈的風聲,克烈的手指還沒伸出,那東西已經逼到他要害。
驚而不亂,那如狐男子反應竟也狐般狡黠,猛一偏頭讓過第一波攻擊,并不去管落空之後立即轉折追來的胡桃暗器,伸手就去抓顧南衣懷中的顧知曉,張開的五指,閃耀着鐵青的暗光。
顧南衣果然立即抱着他家知曉飄身退後,胡桃落地,與此同時一卷銀白的發也蓬然散開飄落――剛才僅憑這擦身而過的圓溜溜的胡桃勁風,便将克烈的一截頭發割斷。
如果克烈反應慢一點武功低一點沒有去攻擊顧南衣的必救,此刻也許斷的就不僅僅是頭發。
這一手看在滿帳族長眼裡,頓時更被震得鴉雀無聲,鳳知微卻終于正眼看了克烈一眼――剛才這兩下看似簡單,但克烈表現出的非凡武功和準确應變令人心驚,他竟能一眼看出她武功不低,沒有試圖攻擊她去挾制顧南衣。
兩人目光相遇,一個微笑一個媚笑,各自有各自的平靜和深意,随即鳳知微閑閑轉開目光,克烈臉色卻微微變了變。
“克烈小心肝……”劉牡丹沖了上來,伸出狼爪就去摸克烈的臉,“好久不見你了,想死你幹娘我了,來摸摸……”
克烈一拂袖拂開她沾滿油光脂粉的手,唰一下退後三尺,笑道:“幹娘您幾日不見,真是青春逼人,美得克烈我在你面前站不住……”
“真的嗎?”劉牡丹喜笑顔開的摸着自己的臉,半怅惘半得意的道,“哎呀,老咯老咯,老公都死咯,劄答闌都娶老婆咯……”
“老公死了正好方便,劄答闌就更無所謂了,他不是十歲就有老婆了?”克烈微笑一瞟鳳知微,“這一帳篷裡,一半都是他丈人……”
“呸!”劉牡丹啪的一巴掌就拍出去,“什麼便宜丈人!克烈你少給我岔話題,來給老娘摸摸,你那小蒜瓣兒長成蒜頭沒?”
“……”
兩人一進一退一追一跑,竟然就這麼退出帳外去了,鳳知微退後幾步靠着帳門,饒有興緻看她家牡丹花纏上白狐狸――流氓交給花癡來磨,那是最合适不過了,一邊又想,十歲就有一堆老婆,難怪赫連铮三天不去院子就恨不得上房揭瓦,發育得小狼似的,某些方面真是啟蒙太早啊……
“劄答闌!”帳内顧不着這邊的鬧劇,弘吉勒怒喝聲裡已經少了幾分底氣,目光不住梭巡向帳外,“金盟是各族族長議事,你便是順義王也無權幹涉,還不趕緊退出去!”
赫連铮望也不望他一眼,端着酒杯,不急不忙下座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