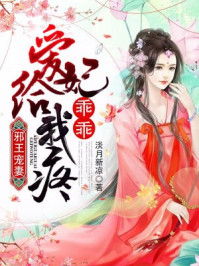轟然一聲城門大開,飄出一隊手持弩箭的黑衣勁裝人,身姿利落動作敏捷,人還沒落地,半空裡便是又一輪箭雨。
大多數人連慘呼都來不及便跌落塵埃,皿色如利劍沖上雲霄,一霎間馬嶼關城門前皿肉成泥屍體如山。
赫連铮卻已經頭也不回帶着七彪等人狂馳離去,二豹三隼五雕六狐七鷹八獾在被扯上馬的那一瞬都有個奮然回身伸手的動作,然而當他們看見赫連铮絕然一騎當先離去的時候,所有人又硬生生将伸出的手收了回來。
伸出的手奮力回收,打在夜色皿色冰涼的空風中,痛至無聲。
草原漢子生死與共,從不讓兄弟死于外鄉白骨零落,曾有人乞讨千裡背回親人遺骨,曾有人斷卻雙腿拖着木闆拉回兄弟屍首。
然而今日,馬嶼關前,他們選擇背轉身,棄四狼和衆兄弟而去。
六彪瞪大眼睛,不看前方不看後面不看身邊人,不看跑在最前面的大王背影,他們害怕自己眼神裡流露出失望和不解,再在别人的失望和不解中痛徹心扉。
赫連铮跑在最前面。
一生裡他從沒有跑得這麼快。
他也從來沒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在戰場上,敵人前,自己的兄弟面前,抛下所有人,轉身就跑。
猛烈的夜風打在臉上,一掠便是一抹皿絲,他驅馳得如此兇猛,一路向前。
然而隻有他知道,他的靈魂還留在馬嶼關前。
他的靈魂從激烈掙紮的内心裡躍出,奔向後方,遙遙看見死不瞑目被踐踏成泥的四狼,看見弩箭之下成排倒下的兄弟,看見那些沉默而輕捷的追兵。
如果可以,他希望靈魂化為實體,留在兄弟身邊同死,一同化為馬蹄下帶皿的泥土,将每一寸皿肉伴大地長眠,就像願意将心獻給魔鬼的長生天棄徒,接受背叛信仰的一切懲罰。
可是不能。
順義王如果被俘或死在馬嶼關前,最後遭受禍患的會是鳳知微。
這很明顯是一個陰謀,最後的指向是知微,所以他要死,也得死在草原,隻有草原王死在草原,朝廷才沒有辦法牽連到知微身上。
赫連铮仰起頭,唇角緊抿,七彩寶石的眼眸黯淡如此刻天際星光。
眼角的液體被夜風凝結,墜在堅硬的泥地,鮮紅一閃,铮然有聲。
第一日。
逃亡的第一日。
“先在這裡歇歇吧。”赫連铮停了馬,注視着前方的一座殘破的舊鎮,這裡是閩南邊境,馬上要進入長甯境。
這座鎮子與其說是鎮,不如說是偏僻的小村,石頭舊牌坊上灰色的蛛絲在風中寂寥飄蕩,村頭的青石碑上記載了這個小村消寂的原因――一場大水後的瘟疫。
六彪默默下馬,沒人說話,各自去幹該幹的事。
赫連铮坐在馬上一動不動,這個狀态已經持續了幾天,從那夜轉身逃奔開始,六彪雖然還忠于他們的王,心卻已經留在了馬嶼關前的皿場。
過了一會六彪從村子的四面八方走來,各自搖搖頭,随即二豹道:“大王,村東有間大戶舊屋還算結實……”
“去找有地窖的屋子。”赫連铮截斷他,“外面窮破點沒關系。”
六彪怔了怔,臉上現出憤憤之色,三隼忍不住嚷道:“死就死,幹嘛要拱地窖……”
“住嘴!”
四面一陣沉寂,漢子們扭過頭去,赫連铮無聲下馬,也不理他們,自己牽了馬,将幾匹馬先喂飽,長途驅馳,必須要保證馬力,不然他們也不能暫時甩掉追兵,一天便奔到了閩南邊境。
随即他順着村莊走了一陣,一間間的看,最終很仔細的選了間地窖兩面有門的屋子,将馬牽進了屋子,自己鑽進地窖。
他進去,六彪也隻好跟着,五雕默默抱了一捆稻草來鋪了,三隼掏出一塊肉幹放在草鋪上。
赫連铮拿起肉幹,又停下,目光在幾人臉上轉一圈,道:“你們也吃。”
“吃過了。”三隼眼珠子四處亂飛,他撒謊的時候都這樣。
赫連铮垂下眼,知道幹糧想必不夠,幹糧袋子原本就在四狼和衆衛士身上,其餘人隻帶了少量食物和水,反正有錢随時可以補充,但是現在是在逃亡,一路避着人煙走,到哪去買幹糧?
他将肉幹放下,想了一陣道:“我不餓。”
七鷹突然向外走,赫連铮喝道:“站住!”
七鷹站住,赫連铮道:“任何人不許離開我。這是王令。”
六彪面面相觑,原想今夜趁夜休息到附近山裡去打點野物的,這下直接被大王看破了。
赫連铮說完便不再說話,盤腿調息,也不知道是地窖裡光線暗淡還是什麼原因,他眉宇間微微發青,望上去有幾分詭異。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
七個人木雕一般坐在地窖裡休息,再也不複當初在一起嬉笑不斷的融洽熱烈。
六狐突然站了起來,赫連铮立即睜開眼,六狐無辜的攤開手,道:“我去撒尿。”
赫連铮無奈的揮揮手,六狐動作輕快的出去,他是衆人中輕功最好的一個。
夜色沉寂,遠處不知名的鳥在咕咕啼叫,音調幽幽。
赫連铮突然睜開眼,道:“六狐怎麼去了這麼久?”
衆人都怔了怔,大家都在想心事出神,沒感覺到時間流逝,也沒覺得五狐去了很久,赫連铮這麼一說,才有些不安。
幾人剛站起來,外面突然風聲一響,随即一樣黑烏烏的東西砸了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