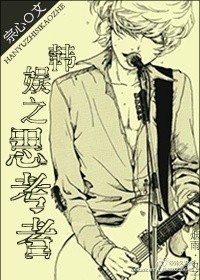洛中近來氣氛微妙,特别梁王一家更是時流所關注的焦點。
為了免于族人們做出什麼行為被人過分的解讀或是給人以誤解,梁王府近日來也是加強了對洛中族人的約束。包括那些本就乏于謹慎的少年們,索性便給直接拘禁在府中,不許随便外出。
少年心計單純,性喜玩樂,能有機會免于學業辛苦自然是好,但卻又禁足府中,更兼王妃主持家事,近來多有裁用,則就難免加倍的枯燥。
天中義骨沈二郎最近這段日子過得很不舒心,總覺得世道諸人無論認識的又或不認識的,似乎都在有意無意的為難他。
不必再望學府進學,這一點沈勳倒不怎麼在意,畢竟學業對他而言也隻是副業。但是每天不能按時入學,卻直接妨礙了他制霸龍門的雄圖。
最近這段時間,河洛氛圍本就略顯浮躁,就連館院許多學士都熱衷于在龍門辯場揚聲競雄,那些年輕氣盛的館院學子們無疑更加狂躁,約鬥之風較之往常頻繁數倍有餘。而且由于館士院士們各自忙碌,也讓館院這段時間學規不如往常那麼嚴謹,對于熱皿上頭的學子們而言,更不啻于一場狂歡。
這種時刻,正是沈勳這種激情過剩的少年最為鐘愛的,可偏偏他被拘在家中,心情之落寞如雪可想而知。
每每館院同窗入府來見,聽到那些人眉飛色舞講起龍門峥嵘事迹種種,沈勳更是心癢難耐,黯然自傷,待到同窗告辭離開之後,便活力全無,獨居室中仔細擦拭他那些與主人一般寂寞的兵尉杖,隻覺得蜀先主劉備感于髀肉複生而垂淚,那種傷情也恰如此時。
沈勳不是沒有嘗試過私逃出府,但結果就是僅僅隻為了防備他一人私逃,梁王府内外護衛力量便增加數成,居室内外常有十數人衆監視着他。
特别在某次從遊園水塘暗渠被家人們打撈上來之後,适逢他大父沈克正居府上,與前來拜訪的他家大舅賀暢比較認真的讨論是否有必要暫時将沈勳腿打斷拘養在府中,沈勳才意識到這些老家夥是真的心狠手辣,自此鬥志消頹,變得安分起來。
如果被真的打斷腿,疼痛與否還在以此,若真遭如此毒手,就算他逃出去也無複舊年雄風,現身人前也不過徒增笑柄,這是對自身形象要求極高的沈二郎所不能接受的。
不能出府參與館院械鬥還在其次,對沈勳而言人世艱難卻還不止于此。早前他驚聞噩耗,原本館院學子們于伊阙籌建的義園竟然被人強占!
原本對于館院學子們湊趣籌建的這座義園,沈勳是不怎麼在意的。但無論在意與否,天中學府一衆時人哪個不知此園與他沈二關系不小?
臉面被人如此羞辱,沈勳又豈能忍受,得訊之後即刻便請人傳話召集館院諸友,他自己也打算親自現身去狠狠教訓對方一番,也正是被家人堵在水塘暗渠、進退不得而被打撈上來那一次。
那一天沈勳沒能成功溜出,心情可謂悲怆有加。一直過了幾天,他才得知後續消息。那一夜他雖然缺席,但館院少流卻也素來都沒有忍氣吞聲的習慣,放學之後集結數百之衆,各持器杖浩浩蕩蕩往義園而去。
但是,結果則更加悲怆。當這些學子們抵達義園的時候,才發現他們的對手超乎尋常的強大,足足五千名駐洛王師!除此之外,還有行台大長史杜赫等高官,包括馨士館接替範汪擔任新館長的孟嘉等一衆學士。
沈勳雖然沒有親自到場,但哪怕僅僅隻是通過同窗時候描述,也能想象到當館院數百學子突然出現在整整五千駐洛王師并一衆行台大員和館院學士們面前時,是怎樣一種飛蛾撲火的壯烈!
當時情境如何,已經不可細言,反正一直到現在為止,那天出現在義園外的學子們課業加倍之餘,還要負責整個學府區的灑掃清理,這一樁懲罰,據說将會一直持續到他們結束學業。
總之按照同窗的描述,當時新館長孟嘉臉色濃黑如漆,那也就注定在館長卸任之前,那些學子們隻要一日還在學府進學,都不要再想有好日子過。
之後發生的事情,也讓這些學子們更加絕望,原來隐藏在背後、他們真正的對手竟是梁王!梁王劃定伊阙一片區域為義主立祀,而義園正巧落在範圍之内。
如果不是梁王之後發聲,稱贊了學府少流尚義之風,這件事也沒有那麼簡單收場。
不過館院學子們這一次的集體翻車也不是沒有正面的收獲,他們原本那種約鬥風潮也算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可,甚至在義主祀園中專門給他們留了一處場地,一如時流賢士們出入的龍門議場,甚至于就連各種搏擊技藝都因此進入館院課業之中,不乏軍中老卒入此執教。
但無論後續發展如何,那悲壯的學府五百義士每天忙碌的身影還是固定出現在學府各個區域。這是館長治學權威體現,哪怕梁王和行台都不會随便幹涉。
對于自己的缺席,無論是何種原因造成,沈勳都有些不能釋懷。雖然也托同窗慰問補償,但每每思及,還是難免神傷自慚,覺得自己辜負了義氣,已經不再是往年那個純粹、資深的義氣兒郎。
少年不知愁滋味,将知于愁,便覺深愁。除了堆積在心中這些愁緒之外,沈勳還有其他困擾,那就是居家這段時間,他的阿母賀氏對他突然又關心許多,每每召他入室陪伴。若隻如此還倒罷了,沈二郎雖然推崇義氣,但也并非罔顧孝道,起居殷勤問候都是應有之義。
可是讓沈勳有些受不了的是,他在陪伴阿母的時候,往往會遇上洛中其他人家家眷來訪。每每這時候,沈勳便想抽身而去,卻不被阿母所允,隻能繼續無奈作陪。可是他對那些帷閣婦人話題是完全提不起興趣,根本就懶于去聽。
那些各家眷屬,往往會攜子女同來,沈勳便要負責接待他們。若是少年郎還倒罷了,沈勳可以跟他們講講學府求學轶事,不着痕迹炫耀一下自己于學府威名,或者帶他們欣賞一下自己的器杖珍藏,逛逛府内馬場、射堂,再加上去見一見阿秀等堂兄弟們,也算能應付過去。
最讓沈勳感到頭疼的,還是各家跟随長輩來訪的女郎們。這些小娘子,一個個嬌滴滴的,請她們騎馬較射完全就是白費力氣,講起學府轶事她們也不感興趣,卻偏還要裝出一副很感興趣的模樣追問不休,實在讓人煩躁不已。
特别有一次,平原華氏家人來訪,沈勳又被安排陪伴華氏小娘子。那小娘子相貌如何,沈勳已經忘了,但至今想起仍懷餘忿,當他講起學中轶事,那小娘子居然勸他要自愛惜身,不要傷了自身而讓長輩擔心!
這實在是太過分,那小娘子根本就不知沈二郎在學府是一個怎樣存在!哪怕館院之中最骁勇善戰之人,也沒有膽量還未開戰便如此小觑他會必傷!
所以沈勳當時便怒了,耐心消磨殆盡,隻是遺憾這小娘子不是男兒身,不可角力競勇,但當時沈二郎也放言讓那小娘子可随意指派壯力家人下場較技,看看能否傷得到他?男兒志力,豈可輕侮!
那小娘子自知失言,掩面泣去,從此後便不再見。這也讓沈勳找到一個免于此類煩擾的好方法,想要評價他沈二郎技藝如何那也簡單,先選自家壯士角力一番。若連一戰的勇氣都無,還是乖乖閉嘴,勿為厭聲!
如是幾次,他家阿母便也不再熱衷讓他陪伴,沈勳便樂得自在,每日騎馬習射,務求拘令解除後再現身人前時,技藝上能有一個令人驚豔歎服的長進,讓那些館院同窗知道他沈二郎絕非虛度光陰,仍能領袖于同侪!
人若能精誠專心于某一事物,時間則也變得不太難捱。沈勳整日泡在射堂,漸漸地心情反倒變得平靜起來。
這一天,他仍在射堂習射,剛剛射完一壺箭,便見堂弟沈綸正搖頭晃腦行來,沈勳笑呵呵道:“麒麟來得正好,我聽我家六郎與蒲生說你常在府内笑我不如阿爺遠甚。早幾日去尋你不見,今天正巧,你來,咱們兩人較技,我縱然比不得自家阿爺,難道還收拾不了你這小子,看你還敢在外譏我!”
沈綸聽到這話,臉色頓時垮了下來,轉身欲逃卻已經被沈勳于後方扯住衣帶,忙不疊轉頭谄笑,又一臉無奈道:“那幾個無知小子,便溺都難自理,二兄你怎麼能信他們?就算、就算我說過此類話,那也不是笑你力技,伯父可是世道推崇的英流丈夫,說你不如,也不是辱沒你……”
沈勳卻不理這小子狡辯,還待要下手用強,卻聽沈綸大聲叫嚷道:“二兄難道不想知咱們何時能解禁足?我可是一打聽到消息便來尋你……”
聽到這話,沈勳眸子頓時一亮,狠狠敲着沈綸額頭獰笑道:“打聽到什麼?趕緊道來,你若欺我,嘿嘿……”
沈綸掙紮着爬起來,頗有幾分不忿的張張嘴,終究還是不敢太硬氣,畢竟眼下都在府中,他可沒有同窗勇力可恃,隻能低頭道:“我打聽到的,自然是一樁大事!之前與阿秀并讀書廬,阿秀講起一樁大事,言是秦皇故玺歸國,乃河北義士投獻,已經入了行台。眼下咱們兄弟,唯你最得大王青眼,早前圈選義園供祀義主,那是為了助你揚名。阿秀着我告你,若想長于見識,便速去乞求大王,說不定咱們兄弟都能承惠往行台瞻仰國器風采……”